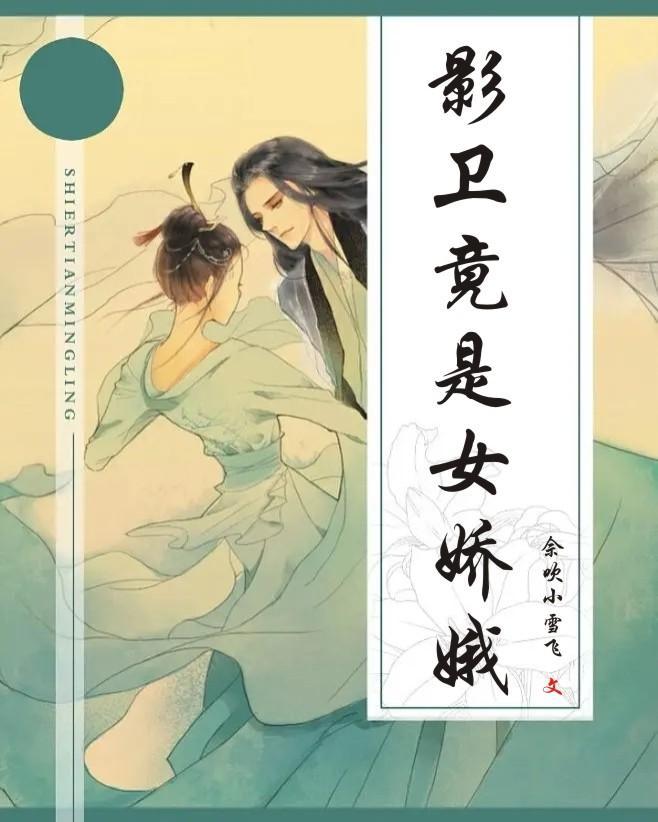富士小说>当我另嫁他时裴彧 > 第 20 章 宋娘子她亲了贺女郎还(第4页)
第 20 章 宋娘子她亲了贺女郎还(第4页)
跪地的婢女眼中挣扎两下,忽而伏地磕头,害怕道:“还有一事,奴婢不知道该不该说?”
僮仆双眼一瞪,斥道:“少将军面前还敢隐瞒,还不快如实禀告。”
“那日贺女郎落水,没了生息,衆人没了办法,是宋娘子,她……”
僮仆追问:“宋娘子怎麽了?”
婢女双眼一闭,咬牙喊道:“宋娘子她亲了贺女郎,还亲了贺女郎好几口,然後贺女郎就活过来了。陶媪不让我们乱说,不然就要发卖出去。”
她说完也觉察不对,宋娘子是少将军的妾室,居然亲了旁的女人,这传出去于少将军可是奇耻大辱。
婢女瑟缩解释:“宋娘子是西王母转世,她亲两口就能将人救活,她是神女,不能罚她。”
“闭嘴吧你!”僮仆擦着脑门上的汗,从这婢女开口说出宋娘子亲了贺女郎开始,少将军的脸色就变得极其古怪起来,有好笑,有无语,还有几分他看不懂。
随後,他听见少将军吩咐:“都下去吧。”
僮仆带着婢女离开,他心中有几分不忍,他自幼伺候少将军,看他独身一人到二十岁,好不容易有个知心人陪伴,没料,唉,也是可怜。
僮仆回望身後紧闭的房门,他见过宋娘子,是他此生见过最好看的女娘,可惜了。
不管贺佳莹和裴彧处有多热闹,徽音舒适极了,她回了临水阁,吃着酒酿,悠哉游哉的躺在矮榻上看策论。
用过午饭,她觉得有些困倦,躺在矮榻上舒舒服服的睡到申时,远眺湖景。
平桢,确实给她很大一个惊喜,他是平太後的娘家人,还是平家三房的独子。
平太後是当今陛下的生母,她年轻时和已逝的章太妃斗法,失败後被贬入冷宫,受尽宫人磋磨。先帝在其入冷宫後将年幼的陛下教给章太妃抚养,是以陛下与章太妃更亲,而与平太後这个生母不亲。
陛下登基之後将平太後从冷宫接出,与章太妃平起平坐,平太後因此与陛下冷心,不论陛下如何补偿都不原谅,搬进永寿殿,不问世事。
章太妃去後,陛下也越发怜惜这个生母遭遇的苦难,屡次提拔平家,想要修复母子之间破裂的关系。
利用平祯得当就能顺利将苏信拉下马,只是此事,她需要好好计策,那萧纷儿她未曾见过,从贺佳莹口中能看出来她是个娴雅文静的女子,这样的女子怎会与人通奸,还是苏信这样的膏粱子弟。
事关女子声誉大事,稍有不慎就会危及其性命,须得慎之又慎。
此时无事可做,徽音遂让颜娘将六博棋盘拿出来,带着阿桑和阿蘅玩六博戏,玩到一半,院门口传来一声喊叫:“宋徽音!”
裴衍正处在变声期,一把嗓子沙哑又难听,异常好辨认。只是徽音听见他的声音就脑袋大,不会是被裴彧罚了一顿,特意来找她麻烦的吧。
她本想置之不理,奈何院外那人不达目的不肯放弃,扯着难听的嗓子继续吆喝:“宋徽音!我知道你在里面,别装死!”
阿桑和阿蘅面面相觑,她们自幼长在裴府,自然知道这声音是谁。颜娘就没那麽客气了,没好气的穿鞋开门:“谁啊,没半点规矩,宋娘子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
她拉开门,面前凑上一张笑嘻嘻的大脸,赫然是那日拿弹弓击打她和徽音的裴衍,颜娘看见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徽音膝上的乌青到现在还没消,她擡手就要关门。
被那少年擡手挡住,他虽年少,力气却不小,又学过武功,三两下就制服颜娘闯进院内。
阿桑和阿蘅见他到来连忙起身相迎,裴衍挥挥手,捧着手中的漆木盒走到屋外,朝着端坐的徽音作揖行礼,“我今日是为那日伤了你来赔罪的。”
徽音稳坐不动,擡颚示意他看向身侧的颜娘,裴衍转头看过去,没看到什麽东西,他摸着脑袋不解:“什麽意思?”
“你那日不止伤了我,还伤了我傅母,傅母是我在这个世上最重要的人,你先向她道歉。”
裴衍也想起来了,他整整衣襟,转向颜娘,神色恭敬作揖赔罪,“那日全是小子的不是,还请原谅则个。”
颜娘无措的不知手脚如何摆放,她跟在徽音身边虽没受过刁难,但被贵人冷待讥讽是常有的事,从没有贵人恭恭敬敬的向她赔礼道歉过。
在他们这些贵人眼里,奴婢的性命还不如他们衣裳上的金线重要。她侧身避开这个礼,轻轻点头,跪坐在徽音身後。
裴衍看向徽音,将手中的漆盒递给阿桑让其转交,“今日阿兄狠狠的责罚过我了,我也知道我那日错的离谱,不该伤人,今日特来请罪,望徽音阿姊原谅。”
徽音打开漆盒,里头放着一只竹编的蜻蜓,手艺略有些粗糙。
裴衍不好意思的摸着头,解释道:“我想来想去,还是觉得得亲手做些赔礼给你,这竹蜻蜓是粗糙了点,你可别嫌弃啊。”
徽音取出竹蜻蜓,举在手中端详良久,而後笑道:“我很喜欢,也原谅你了。”
裴衍松了口气,喜欢就行,不枉费他花了大价钱买来的紫竹。他又想起那日对徽音的出言不逊,还说什麽不会承认她是嫂嫂的话语,顿时脸色灰败,不知道该如何挽救。
见徽音一脸微笑的看着他,裴衍扭扭捏捏的扔下一句话跑开:“我那日说的都是气话,你人还不错!”
徽音看着他远去的身影,心情甚好,将竹蜻蜓收好放在漆盒中,交代颜娘收好。
裴衍虽乖张,但心性还算纯良,缺乏教导,他以往几日都没有想过来道歉,怎麽今日突然来了,是他授意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