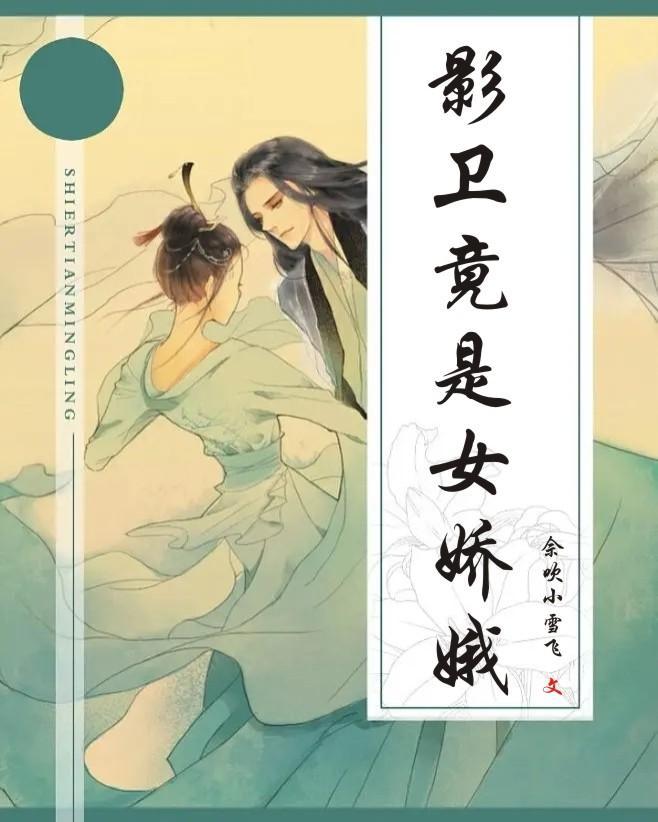富士小说>替嫁以后晋江 > 第55章 第五十五章 哪个男人能得到你的心呢(第2页)
第55章 第五十五章 哪个男人能得到你的心呢(第2页)
她泪水流得更凶,模糊了视线。
世界只剩下马车轱辘的噪音和她自己震耳欲聋的心跳。
羞耻,恐惧,绝望。……无数情绪撕扯着她,几乎要将凌枕梨撕裂。
可凌枕梨没有选择,薛皓庭是薛家未来的掌权者,只有他能够改变薛文勉的想法了,在这个节骨眼若是被薛家抛弃,她就前功尽弃了。
就在这时,薛皓庭目光缓慢地向下移,落在他的……
昂贵的布料下,隐约可见蛰伏的轮廓,他没有说话,只是那样看着,再擡眼睨凌枕梨。
……
凌枕梨沉浸在惶恐失去庇护的强烈不安中,任由薛皓庭按着她的头,强迫她,在那最深处停滞丶碾压。
就在凌枕梨以为自己会被这样活活憋死的时候,他又猛地将她拽开。
新鲜空气涌入肺叶,凌枕梨趴伏下去,剧烈地咳嗽干呕,口水混着眼泪鼻涕糊了满脸,狼狈不堪。
头顶传来薛皓庭冰冷的声音,带着一丝情动前的沙哑,却更令人胆寒:“这就受不了了?你跟房闻洲在一起时,也是这般不济事?”
凌枕梨咳得说不出话,只能拼命摇头。
薛皓庭不允许她逃避,抓着凌枕梨的头发再次将她提起来。
“说,”他声音低哑,命令不容置疑,“你以後该听谁的话?”
巨大的恐惧和屈服感淹没了凌枕梨,她闭着眼,用尽全身力气,含糊不清地哽咽:“听你的话……”
“你该叫我什麽?”薛皓庭对她的答案不太满意。
凌枕梨啜泣着喊了一声哥哥。
薛皓庭稍微柔和了一点,手指摩挲着她的头发:“我想听你叫我一声夫君。”
什……什麽?!
一个两个的都疯了吗?
眼看薛皓庭好不容易缓和的面容又要再次冷峻,凌枕梨垂着脑袋,忍着耻辱烧灼着五脏六腑,喊了一声夫君。
而他步步紧逼,非要凌枕梨看着他的眼睛喊。
“夫君。”
这两个字烫得她喉咙嘶哑,声音小的几乎听不见,但好歹凌枕梨是说了。
他似乎终于满意了,松开凌枕梨的头发,身体重新靠回椅背,用一种睥睨的姿态看着她瘫软在脚下狼狈喘息。
“我原本还以为你真的爱上裴玄临了呢,如今看来你对他的情义也不过如此,也对,你这没心没肺的女人,哪个男人能得到你的心呢?”
凌枕梨听到此话,柔弱也不装了,疲惫地自嘲:“得到我的心做什麽?男人不就是为了得到我的身体吗,况且,比起我的心,得到我的身体对于你来说不是更容易吗?”
薛皓庭笑了,不是愉悦,而是某种掌控她的餍足。
他伸手,粗糙的指腹恶劣地拨弄了一下凌枕梨的脸颊:“嗯,你说得对。”
薛皓庭失去了耐心,不想再听凌枕梨倔强的话,猛地将她整个人从地上提起来,粗暴地翻转过去,面朝着车厢壁压弯下去。
昂贵的锦缎裙裾被他毫不怜惜地撩起堆叠在腰际,下身瞬间暴露在微凉的空气里。
薛皓庭一只手死死压着凌枕梨的背脊,另一只手扯开她身上最後的束缚。
然後没有任何预兆。
突如其来的不适让凌枕梨痛喊出声,指尖下意识地掐入他的後背。
他呼吸沉重,喉间滚出一声低哑的笑,更深地拥紧她,仿佛要将她揉进骨血。
过于紧密的贴合和那不容抗拒的力道让她阵阵发晕,脱力地软在他怀里,发出细弱的呜咽。
“薛皓庭……你又……”
“又怎麽?”
“……”凌枕梨隐忍,撇过头去,不再说话。
薛皓庭不依不饶,灼热的呼吸烫在她耳畔,嗓音沙哑得厉害:“他对你好吗,还是也像我这样?”
“他……没有……”
她破碎的否认与呜咽被无声地吞没,在剧烈的动荡中,意识如断线的纸鸢被气流撕扯抛掷。
感官彻底崩散,只剩下一阵阵失重的晕眩,仿佛下一秒就要瓦解。
逼仄的空间里,只馀两道交织的呼吸,一道是灼烫的掌控一切的潮汐,另一道是细弱的被潮汐彻底淹没的涟漪,断续地,敲打在窒息的寂静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