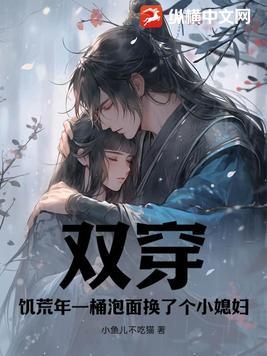富士小说>药膳出处 > 天下初定三(第2页)
天下初定三(第2页)
黎清宴作为王逍瑶的第二任老师,二人十分熟拈,交接的过程相当顺利。
王逍瑶手上的兴复规划十分清晰合理,在黎清宴看来,直接沿用即可。他不准备再额外耗费心神,开始着手准备上任後第一件面向百姓的大事——祭祀战争中亡故的同胞。
祭祀地选在大安镇。
这座紧挨着雁门关的边陲小镇,在战火之中,寸草未留。
王盼儿丶王逍瑶丶沐川在祭祀的日子,重新踏上这片地界。看着曾今商贸发达的繁华小镇沦为一片废墟,心中只剩荒凉。
战争带给人的伤害一辈子都无法抹去。
王盼儿不想徒增感伤,不敢再回想大安镇的那些美好时日。她将视线转移至祭祀的仪式上,不断劝告自己莫要再生愁虑。
斯人已逝,活着的人总得向前看。
祭祀仪式委以严华寺方丈主持。
方丈在雁门关的关口内设了法坛,僧人们依次按礼制摆上三牲五谷与酒醴後,再吟诵祭文与经文。
期间知府官员及自发前来吊唁的百姓依次行礼拜祭。
沐川天蒙蒙亮时就出了门,进山间为王盼儿采来不少野菊,中间还零星夹了几朵彼岸花。
轮到王盼儿时,她接过沐川递来的花束,还是红了眼眶。
她一个异世之魂无法笃定人死之後是否还能有来生,若能有来生,她希望这些战争中亡故的人们,可以平安顺遂一生。
祈愿完,王盼儿将花束摆在了祭坛中间。
主持点了火,这些寄托哀思的信物与祭文经表,统统在浓烟中化为灰烬。
与此同时,晋州府内,苏氏一族唯一的嫡系血脉苏凌雅开了祖宗祠堂,为父亲与弟弟负荆请罪。
圣上仁慈,未诛灭九族,族内未参与私铁一案的人只是尽数被抄了家産。然百姓激愤,除了在营地实打实做了贡献的苏凌雅外,其馀人等皆不被允许进入坊市。
苏氏一族享受了私铁带来的红利,官府设立是为民解忧,黎清宴自觉没有没有立场,也不愿插手百姓之间的恩怨,任由苏氏族人自食恶果沦落至乐户市。
苏凌雅开堂请罪後,终是不忍眼看祖宗的百年基业就此终结,向王逍瑶递上契书与印鉴,以期流云商会能有延续的机会。
好在王逍瑶深得民心,又有嘉义县主的身份加持,她顺利接过了流云商会的盘子,并坐稳商会会长的位置。
商会中存了不少充数的臭鱼烂虾,王逍瑶重新清理了会籍,指定新的入会标准,然後向许多在流民营地出了力气的商铺递上了她的邀请函。
流云商会改头换面後,山河药膳馆成了核心的初始会员,在百姓的拥蔟中悬挂好圣上亲题的牌匾,重新开张。
山河药膳馆还是那个山河药膳馆,菜谱没变,夥计也没变,唯一的变数是在大门侧边坐诊的大夫换成了新的面孔。
深受百姓爱戴的陶大夫,带着徒弟们上了前线,在军营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已有名徒弟可以单独坐诊了。尤其王澄曦开了口後,更是被陶妁视为可以继承衣钵的亲传弟子。
她如今完全退居二线,潜心专研女科和教习事业,由弟子们在山河药膳馆轮班。
至此,所有人的生活重新步入正轨,晋州府城在黎清宴的规划下,也运转如从前。
沐川收拾了行囊,必须回京了。
他有他需要担负的责任与使命,陪伴王盼儿度过最艰难的时光後,就不再容许自己耽溺儿女情长中,滞留晋州府内。
这次王盼儿没有准备与他一同回京。
经过深思熟虑,王盼儿确定目前的自己还是不能适应上京的贵女生活。
她只是看起来随和,实际内心与沐澜一样,都是向往自由的放飞状态。上京势力盘根错节,以她目前的实力,并不能够施展拳脚。
在长公主的荫蔽下,她能活得闲适且安逸,但拥有自己的事业,体会过在自己领域中掌握绝对话语权的滋味後,这样的生活难免会带来令不愉的束缚感。
王盼儿下定决心,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节奏生活。她想要一边游山玩水,一边将山河药膳馆的分号开遍大夏,最後开到京城,落地生根。
届时,她才能以完全舒适的状态在皇城脚下站稳脚跟。
况且她已有郡王妃的身份和长公主府的背书,加上天成元钱庄取之不尽的钱财,直觉告诉她,这一天绝不会远。
![网恋对象掉马后[网游]+番外](/img/76591.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