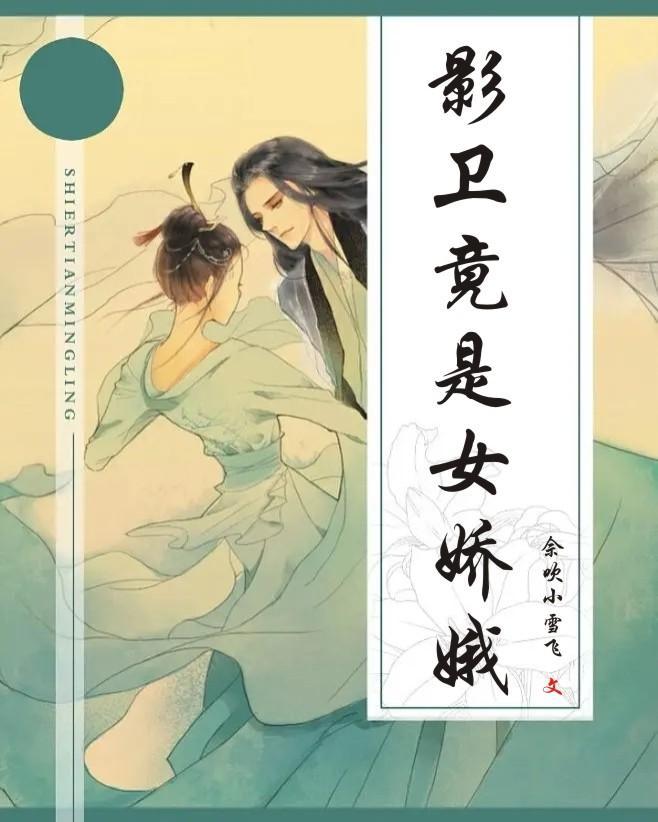富士小说>星光下的梦想原唱郭易 > 番外 或许我们都不勇敢番外(第2页)
番外 或许我们都不勇敢番外(第2页)
她总是太习惯撑着,像是怕一软弱就会被什麽拖进深渊。
我不想说那些安慰的话了,怕她觉得我在妥协。
这次我们争执的不是什麽大事,但她说,“你怎麽也不站在我这边。”
那句话听进来,不像玩笑。
其实我本来就站在她这边,只是没照着她要的方式去表达。
我偶尔也会为我的嘴笨感到厌烦。
但现在讲什麽都多馀了。
她靠在我肩上,呼吸轻得像羽毛扑过皮肤,心里一下一下地被搅动。
她的手还抓着我外套下摆,不知道是不是不小心。
毕竟喝酒都会想找个支点撑住自己。
我侧头看她,想伸手去拨一下她的头发,却在即将碰触的那一刻收了回来。
我们现在的关系,好像不适合。
其实也不适合这麽近。
她眼睛没闭,但也没看我。
“Alva。”我喊她的名字,声音比我想像中还低沉。
她擡头,眼神像刚醒。
我几乎要说出口了,那句压了好久的话,像绳索拉到极限只差临门一剪。
但她眼神里闪烁的那一下,提醒了我,我们还在吵架。
我笑了一下,低头看着自己掌心,然後说,“没事,这里冷,记得穿外套。”
她点了点头,没说话,只是轻轻靠得更近了一点。
音乐声慢下来,酒吧里的人开始离席,气氛也跟着松懈。
我们像被困在某种温柔的真空,什麽都没发生,却也什麽都可能发生。
她说她不想回家,但也没说想去哪。
那就,回我家吧。
明明已经恍惚了,却还能正常行走,真挺像她的作风。
车子行驶在空无一人的马路上,她的头轻轻靠着车窗,再慢慢滑下来,撞到安全带,像一张快没电的纸飞机。
我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忍不住把她身上虚盖着的外套拉高点。
车开进地下停车场,熄火後我转头看了她一眼。
她微微睁开眼,眼神在一瞬间与我对上。
我很确定她醉了,不知道为什麽会这麽笃定,也许只是因为那眼神不再有刺。
晚上,我把床让给了她,我睡沙发。
睡前,我去房间看过她,也许是刚刚跟马斯齐斗嘴的小插曲,她现在已经进入了梦乡。
我轻轻把门关上,转身走到客厅的落地窗前。
今夜的星空,挺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