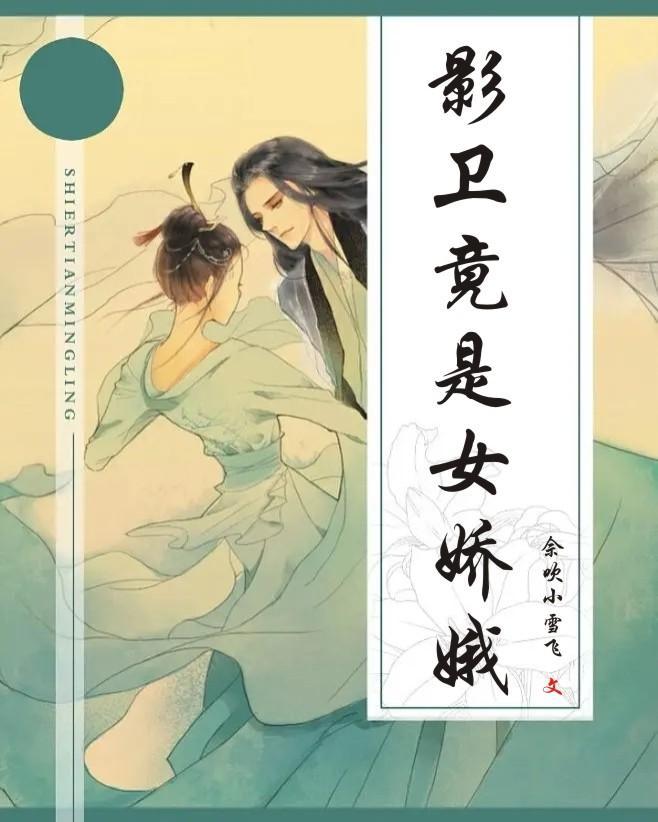富士小说>瞻云就日 > 第32章(第2页)
第32章(第2页)
薛壑把他剥的花生都吃了,冲他点点头,催他继续剥。
只要薛九娘入宫,明烨临不临幸她都不重要,他日查彤史自会有薛九娘的名字。
“那孩子呢?”薛允剥了两颗又停下,转念想过眼睛瞪得更大了,猛地一下站起身来,“你前段时间向明烨要育婴堂竟是这个意思?”
“玉霄神殿。”薛壑吃花生吃得口干,一口枣茶入腹,清甜又熨帖,纠正叔父的四个字从口中吐出更觉唇齿留香。
花生,红枣,早生贵子。
薛壑看着手中的茶水,如果她还在,他们应该也有孩子了。
书上说生孩子是最疼的,那肯定比长智齿还疼。
那她得哭成什麽样子?
茶水中现出一张面庞,少女捂着半边脸颊,薛壑笑起来,却忍不住蹙眉,突如其来的一阵心悸。待他合眼缓过,因手微颤,茶面荡起涟漪,少女的面容破碎,消失不见。唯有薛允的声音回荡在他耳际。
“叫甚都无妨!”薛允环顾四周,复又重新坐下,压声道,“明烨好歹是承袭承华帝遗诏丶改姓入宗继位,如此他的血脉自然算得江氏血脉,但你这会随便用个捡来的孩子,实乃混淆血统!”
“你不说我不说九娘也不说,谁人能知晓?”薛壑将茶盏搁在一处,忽就没了再饮的兴致,只淡淡道,“九娘入宫受君恩雨露,未几天子暴毙。後有彤史为证:薛皇後身怀龙裔。此後孕期,我们无需担心她是否会被害滑胎,生産之时我们也无需担心是否能平安産子。我阅了很多妇人妊娠的典籍,怀胎生産,乃妇人一只脚踏入鬼门关,更有母子届亡的可能,所以没必要冒这重风险。何论这样一来,叔父方才所说的,什麽九娘日久生情丶母子连心就都不存在了。”
薛壑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仅插入了一个掌彤史的女官,就将赢面掌握了七八。然这只是到孩子呱呱坠地,来日还要抚养他,辅弼他;他于世人眼中,到底是明烨的孩子,届时若不告诉他身世真相,就得防明烨党馀孽的渗透,就需要一波波的杀人;若是告诉他真相,他会不会又去寻亲归宗……这条路崎岖无止境。
“你要搭上你的一生。”一时间,薛允连说这话都觉得艰难。
“叔父!”薛壑擡眼看她,“您见过九娘几回,您觉得她像殿下吗?”
薛允毫不犹豫地点头,“要说那张脸是不像,但我头一回在这处见到她,正好她从屋内出来,我瞧了个侧影,拐道下楼又瞧见她背影,我真是被唬了一跳。大白天,我都当太女殿下回来了。”
薛壑叹了口气,凑近薛允道,“我真的太蠢了,就这会功夫突然想到,原有更简单的法子守住江氏江山。”
“什麽法子?”
“我直接让她易容成殿下啊。殿下真身在前,我薛家军在後,谁敢不从。”
屋里熏炉中还燃着香,一阵阵弥散开来。烛火本就点得少,这会又烧去两盏,视线更暗了。
薛壑融在这晦暗室内,月光也照不进来。
薛允辨不清他神色,只仿佛见得他眼神癫狂又清醒,矛盾至极。说的话也分不清到底在论谁。
“那女郎不懂朝政不要紧,我懂。她只要独坐高台,不必沾风雪,我可以一辈子跪伏在她脚下,我不惧一辈子……早在十五岁那年,阿翁就说,她是我一生的意义,我这一生本来就是要献给江氏的……凡我在一日,这天下就必须姓江……”
薛壑没有喝酒,却跌入薛允肩头,语无伦次。
一说,“恐征途太长,此生太短。”
又说,“日日深恨,此生太长。”
说完未几睡了过去。
薛允默了许久,最後灭了近身处的灯,容薛壑倚在他肩头睡着了。
他想了许久,确定从未见过侄子如此悲辛的一面。
原来承华三十三年季夏的太阳被射下後,他再也没有沐浴到日光,日日在阴霾中。
*
向煦台烛火已熄,未央宫椒房殿中却依旧灯火通明。
帝後礼成,宫人全部退出了寝殿。原该是洞房花烛时,然此刻花烛正燃,天子却没有了洞房的兴致。
皇後温柔大方,给他宽衣解带毕,这会正伸手触在他中衣左衽上,还没来得及解开,被静默了许久的天子捏住下颌,缓缓擡起了头。
“陛下怎麽不说话?”皇後笑意温婉,以面贴在他掌心,“可是觉得妾方才所言乃天方夜谭?”
可不是天方夜谭吗?
她将这日黄昏时分,薛壑同她说得计划一字不漏全部告诉了明烨。
“陛下不必忧心,妾可以为您分忧。”她眸光如水,透着精明和算计,“您设宴,妾亲奉一盏酒给阿兄,旁人的他不喝,妾的他不会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