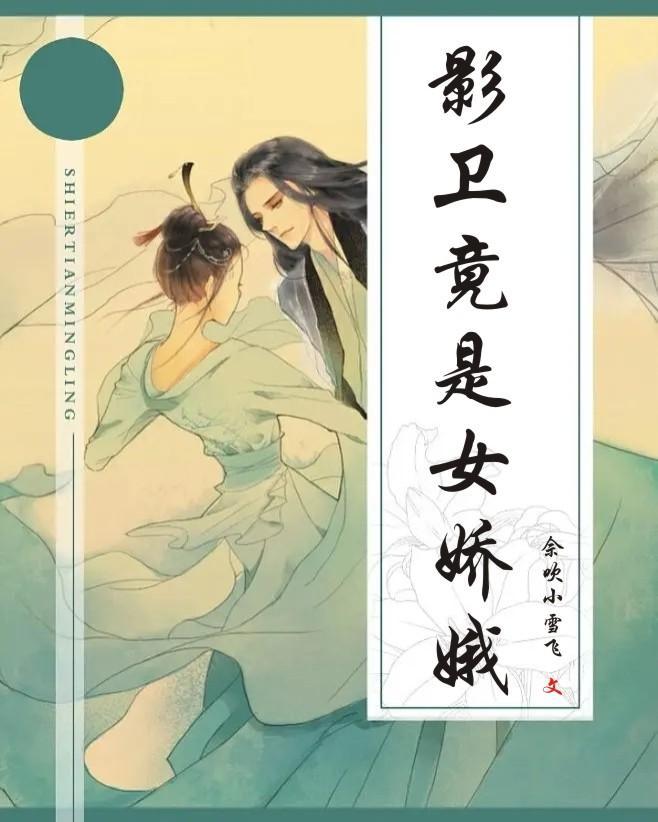富士小说>瞻云酒店 > 第63章(第2页)
第63章(第2页)
……
这日晚间,薛壑在御史府宴请族中子弟。叔父薛允丶薛均三兄弟丶薛墨兄弟两丶还有新上任的薛清丶薛浩丶薛沐等十数人皆在此间。
“过两日便是你生辰了,届时再请不成吗?请在今日,这酒我可喝不踏实。”将将入席,薛九郎便持酒盏叹气,仰头闷了一盏。
“在我府上饮酒,怎就让九哥用不踏实了。”薛壑笑道,“九哥且说,哪里不如你意,十三当下即改。”
“他呀定是盯上了叔母五月来送来的那十来头牛,想着要佐酒。上回就说了,要向你要一头。”薛墨嗓门高起,“我说那是给陛下的,非节非宴吃不上。他就想着你生辰宴定会上这膳。”
“薛七郎,你说你自个吧!”薛九郎从案上拾了薛墨一贯喜欢的冬枣丢过去,边笑边道,“别以为方才入门时我没看到,谁偷偷跑去膳房问膳,被红缨姑姑赶出来了?”
“都拿去给他。今个他吃枣,我吃肉。”薛九郎对着一旁奉酒的随从吩咐道。
“我是想吃,你们哪个不想吃?薛沐丶你想不想?薛清丶薛浩是不是都想?”
此三人虽是同族,却已经是旁支,没有他们那般熟络,来御史府的机会也不多,当下有些拘谨。闻薛墨的话,只含笑不语。
薛墨却还在言语,推一推自己案上已经摆上来的各色菜肴,“这等时节,凡有一鼎烹牛肉佐酒,旁的我都不要。”
“这话是真的,咱们益州的黄牛肉,哪个不想。”薛九郎又叹,“但这会上黄牛肉,着实可惜。”
“哎你这人……”
“七郎莫脑。”薛均笑道,“他呀被尚书台的事缠住了。眼下莫说诸府衙,便是你们禁军轮值休沐不都松快些了吗?但我们尚书台为着官员上任调任的事,至今还未闭衙,陛下的意思最好是在今岁定下,明岁明窗开笔後,便直接上任,不误政事。所以明个我们还得上尚书台。九郎就盼着廿三小年後,无论有无决策,左右都开年假了,他便好吃个痛快!”
“其实八校尉就八校尉,也不知为何要不同意!”薛八郎接了话,“我听说还惊动了大司农处,说什麽把‘节官制’都搬出来了,至于吗?”
“就是!”薛九郎端起面前酒盏,然一想明日还要去尚书台,只好控制着饮酒,夹了一箸符离鸡佐酒,擡头望向正座上的薛壑,“十三郎,你今日到底何事请我们?”
薛壑看见外头侍者擡鼎而来,笑道,“给你们解馋。”
诸人循他目光望去,顿时都抚掌应笑。薛墨当即起身,说是由他来捶肉松气,又唤十六郎过去掐丸。然薛十六郎神色怏怏,薛墨连唤他两回都不得应。
“我来!”薛均看了胞弟一眼,知他近来心情不畅,当下打了个圆场。
送入殿中的牛肉,或打成丸子入鼎内,或切成蝉翼片在汤中烫起,外头还时不时送来炙烤好的牛腿,炖烂的牛腱子,配着烈酒,未几一族的子弟都用痛快了。唯薛允几回看过薛壑,见他案前酒盏,一动未动,这晚他滴酒未沾,话也极少。
至酒酣宴将了,他方啓口道,“故土膳食,诸位可都喜欢?”
“喜欢!”
“喜欢!”
“多少年了,都想着这一口。”
“这隆冬岁暮,就该日日食用方算美妙。”
殿中人你一眼我一语,连着初时拘谨的薛沐一行也感慨道,“用起这肉,便想起了阿翁阿母,我来长安时才十四岁,那年头一回帮阿翁宰牛。”
……
“如此,回去吧。回去可日日用此膳,日日见爹娘承欢膝下。”薛壑坐在高台,淡淡开口。
“今岁我本想回去的,但阿妍五月里才诞下孩儿,我的休沐日都用完了。”薛清道,“待明岁攒一攒,孩子满了周岁,我带他们母子一道回去看看。”
“我今岁也想回去的,就是岳母病了,岳丈又去的早,膝下独阿颂一女。她侍奉榻前,我也不好远离。”薛浩叹了声,“我也明岁看看再说,左右益州有阿兄阿姊他们。”
“你们近来可都有高升,入了南北营中。但回去益州没有一两月休沐不可行,届时要提前和上峰说好,别误了事。”薛墨提醒道。
“我前岁才回去,近来倒也不急了,就是念这一口。”薛八郎将案前一碟炙肉蘸着剁椒酱咽下。
殿中又一番热融融闲谈。
“我不是说回去看看。”薛壑面上沉静无澜,心中千波在涌,“我是说,我们该回益州了。”
这话落下来,殿中一下静了,诸人目光齐齐投去,慢慢反应过来。
“十三郎,你再说一遍。”这日一直沉默寡言的薛十六郎在此刻最先开口。
“我说,我们该离开长安,回益州了。”
殿中又是一番静默,片刻依旧是薛十六郎的问话,“这是陛下的意思吗?”
薛壑摇头,“我的意思。”
他顿了顿,也不再迂回,直言道,“当初我带诸位从益州奔赴长安,就是为了守江氏基业。如今贼人已除,江氏天子在位,我们没有留下的理由,该退回故土了。”
“你说得轻巧。你让我们来就来,让我们走就走。且不说没来赴宴弟兄,你就看看今日宴上人,薛清丶薛浩丶薛沐他们,随你来长安时不过十四五岁,当年为保江氏社稷,你掐尖挑走了族中最年轻最优秀的子弟,这我们无甚可说,理当来此。但是来此六七年,十四五岁後的六七年,你知道有多重要吗?我们在这里及冠丶成家丶立业,好不容习惯了这片土地,可以安生立命,有了另一个家,你却又要让我们回去!”薛十六郎摇首道,“这定然不是你的意思,肯定是陛下,鸟尽弓藏,天子历来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