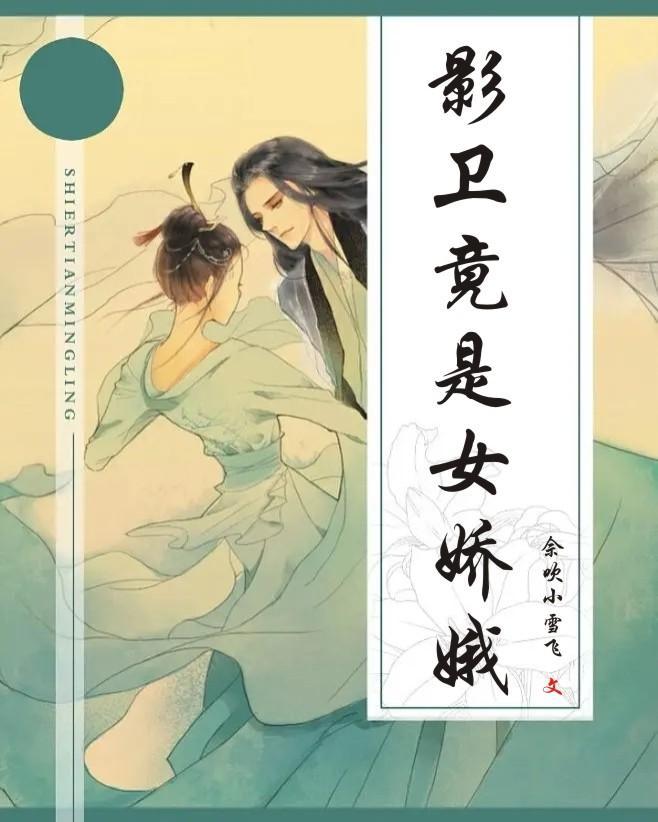富士小说>野酸橘笔趣阁最新章节更新时间 > 第20章 第 20 章 反正恋爱必须谈(第2页)
第20章 第 20 章 反正恋爱必须谈(第2页)
跟他讲理?讲什麽理?他不配她讲理。
“……”秦之屿被哑口无言。
她双标得不仅明显,还明明白白。对谁都礼貌有加,就对他蛮横无理,专治霸道。
梁问夏不是没脑子的傻子,更不是会被随意哄骗的笨蛋。
她当然不会蠢到全信狗东西的一面之词。他惯来不要脸,又抓住她这麽大一个把柄,不可能不夸大其词,趁机栽赃。
她眼睛一眯,怀疑的眼神落他脸上,“你有没有撒谎?”
“没有。”秦之屿面无虚色,说得特别肯定。
他就知道她不好糊弄,肯定会怀疑他话的真假。当然,他也没打算全说假话。
“有没有隐瞒?”
“……”秦之屿从容不迫的脸上裂开一条缝,底气也随之减弱,“有。”
梁问夏听闻立马挺直腰杆儿,“一副我就知道”的表情死盯着他,咬呀怒视,愤然质问:“隐瞒了什麽?”
“我,我说……”秦之屿心里快要乐开花来,面上被装出一副十分难为情的讨厌样。装腔作势,欲言又止,“说不出口。”
“什麽意思?”
秦之屿故意拖长语调道:“你听了,可能会接受不了。”
梁问夏愣住。她现在就接受不了,还能有什麽更接受不了的?
“确定想听?”见她愣神,秦之屿将得了便宜还卖乖进行几个字发挥得淋漓尽致,还是那副勉强的口吻,“如果你实在想知道,我可以勉为其难……”
“我不想知道。”他话都说都这份上了,梁问夏用脚趾头想都知道,他说不出口的是什麽。
不想再听他吐出脏耳朵的话,一句都不想。她不再给他说话的机会,急忙打断,“把嘴闭上,闭严实了,一个字都不要再说。”
秦之屿憋笑憋得腮帮子疼,不敢也不想再刺激她,乖乖闭了嘴。
一连发出三个感叹词,显示自己真的委屈。
“哦!”
“行吧!”
“好吧!”
就怎麽把这件事掀过去当无事发生过,梁问夏陷入了沉思。
不管怎麽样,她跟秦之屿的关系不能变,还是要当朋友的。他俩做了十八年的朋友,要是因为一件意外事件就不做朋友了,她会很不习惯,也不能接受。
她越想越懊恼,没几天他就走了,为什麽要在这个时候闹出这摊子事?早知道昨晚就不该喝那麽多酒,喝多了也不该跟狗东西待一块儿。秦之屿也是个有毛病的,她喝醉胡闹就该离她远点,偏凑她面前来晃个不停。她没那个心思都硬是被他勾出色心来,烦死了。
秦之屿见她一副丢魂了的呆傻模样,用手背轻轻碰了下她脸颊,出声唤她回魂,“想什麽呢?”
她在想什麽?在想是把狗东西舌头割了,还是狠狠心将他揍死灭口。
虽说这两样都能永绝後患,可现在是法治社会,杀人是犯法的呀!算了算了,还是留他一条狗命。
但警告不能少。
梁问夏想到就立即行动,朝秦之屿猛扑过去将他压在地板,双腿骑在他腰间,俯下身掐着他脖子警告:“秦之屿,昨晚的事,你给我全烂在肚子里,谁都不能透露半个字。”
“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要是有第三个人知道,我杀了你。”她恶狠狠地瞪着他,“听见没有?”
秦之屿早算到她会来这招,“我要不答应呢?”
“由不得你不答应。”梁问夏脸上更凶,手上更用力,“你大可以试试,看我会不会将你五马分尸,大卸八块。”
“你这是……”秦之屿未语先笑,伸手扒拉她的手,“不打算对我负责?”
亲也亲了,摸也摸了,睡也睡了,他好不容易得到这麽个能缠上她的机会,会轻易放过?
“把我吃干抹净了,最先想的不是怎麽跟我赔礼道歉,而是叫我守口如瓶当没事发生。”他语气自始至终都平和,末了这句才透着一丝不可置信,“梁问夏,有你这样的吗?”
梁问夏眉心微簇,纠正他:“没有吃干抹净,离吃干抹净还有一段距离。”
“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