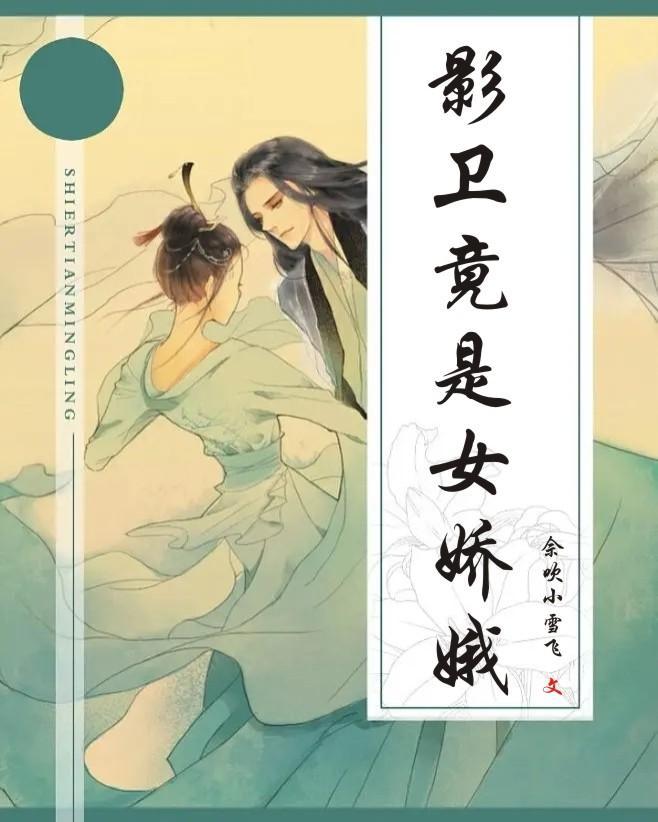富士小说>噬灵蚕最新章节 > 第5章 茅草屋(第1页)
第5章 茅草屋(第1页)
金平河下游的风,带着水汽的腥甜,拂过岸边的芦苇荡时沙沙作响。
王沐躺在茅屋的木板床上,盯着茅草屋顶的破洞呆。
那洞不大,刚好能望见一小片灰蒙蒙的天,几只麻雀扑棱棱从洞边飞过,留下几声聒噪的鸣叫之声。
这茅屋,比他记忆中恒丰典当行的柴房还要简陋。
四面墙壁是黄泥糊的,好些地方已经剥落,露出来里面的茅草和碎麦秆。
墙角堆着半捆干柴,散着淡淡的松木香,一张缺了腿的木桌用石头垫着,上面摆着个豁口的粗瓷碗,碗底还沾着点没洗干净的鱼汤渣。
“醒了?”王有全端着个黑陶药罐走进来,一股苦药味瞬间弥漫了整个屋子,苦得王沐皱紧了眉。
他点点头,挣扎着想坐起来,后背的伤口却猛地扯痛,疼得他倒抽一口凉气,额头上瞬间冒出层冷汗。
“别动,”王有全赶紧放下药罐,扶着他的肩膀轻轻按下去,“你这伤得养些日子,后背那道口子深着呢,再扯裂了可就麻烦了。”
他拿起墙角的粗布巾,蘸了蘸桌上碗里的温水,小心翼翼地擦去王沐额上的汗:“这药虽苦,但疗效甚好,是老头子我上山采的,治外伤管用。”
王沐看着他满是老茧的手,那手上布满了裂口,有的还结着暗红的血痂,想必是常年撒网和劈柴磨出来的。
“多谢老伯。”他声音还有些哑,却比昨天清亮了些。
王有全咧嘴笑了,露出没剩几颗牙的牙床:“谢啥,都是苦命人,互相帮衬着也是应该的。”
他端过药罐,把里面黑乎乎的药汁倒进一个粗瓷碗里,又从灶台上拿起个小陶罐,往药汁里兑了点什么,递给王沐:“蜂蜜甜,能压点苦味。”
王沐接过碗,药汁还冒着热气,一股子浓重的苦涩味直冲鼻子,他皱了皱眉,却是仰头一饮而尽。
苦涩的药汁滑过喉咙,带着一股辛辣的暖意往下走,到了胸口却又泛起一阵翻江倒海的恶心,他强忍着没吐出来,只觉得眼眶都有些烫。
“好孩子,能吃苦就好。”王有全接过空碗,拍了拍他的手背,“当年我家小子也如你这般一口喝下这苦药,可惜……”
他话说到一半,突然停住了,叹了口气,转身去收拾药罐,背影看着有些佝偻。
王沐心里一动,想起昨天王有全说过,他儿子被仙师抓去了,至今生死未卜。
“老伯,您儿子……”他试探着问了句。
王有全的动作顿了顿,过了好一会儿才低声道:“几年前,落霞宗来县里选苗子,说什么有仙缘,其实就是抓壮丁。”
他蹲在灶门前添柴,火光映着他满脸的皱纹,忽明忽暗:“我家石头那时候才十五,力气大,被他们看中了,给硬拉走的,临走时就给了我这几两银子,说是安家费。”
他从怀里摸出个用破布层层包裹的小硬块,打开来,是几块碎银子,边角都磨得亮了。
“三年了,一点消息都没有。有人说在宗里病死了,有人说被妖兽吃了,还有人说……”他没再说下去,只是重重叹了口气,把银子又仔细包好揣回怀里。
王沐的心也沉了下去。
他想起李绝和李浩的嘴脸,想起那些衙役的凶神恶煞,想起段小梅被活活烧死的惨状,想起了枉死的父母和老吴…在那些修仙者眼里,凡人的命,大概真的就像草芥一样吧。
“仙师……”他低声重复着这两个字,语气里带着说不出的寒意,“他们就不怕遭报应吗?”
“报应?”王有全嗤笑一声,摇了摇头,“这世上哪有什么报应?谁拳头硬,谁就是道理。”
他往灶膛里添了根柴,火苗“噼啪”响了两声:“前儿个上游漂下来个矿工,说是在李家矿上干活,矿塌了,腿被砸断了,那些人直接就把他扔到了河里。要不是我捞得快,他早就喂了鱼。”
王沐攥紧了拳头,“李家矿场?是仙师李绝的矿场吗?”
他想起父亲说过,李绝在金平县开了好几处矿场,说是为落霞宗采灵矿,其实多半是为了自己截取修炼资源,那些矿工,怕是没少受磋磨。
“那矿工后来呢?”他又追问。
“除了他们家,还能是谁!”王有全叹了口气,“至于那矿工,我给了他点干粮和药,让他往南走了。在这儿待着,被码头上那些李家的爪牙看见,只能是死路一条…”
他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王墨啊,你也是从金平县逃出来的,该知道李家的势力。等你这伤好了,就赶紧往远了走,别回头,也别想着报仇。”
王沐没说话,只是望着屋顶的破洞,眼神里的寒意越来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