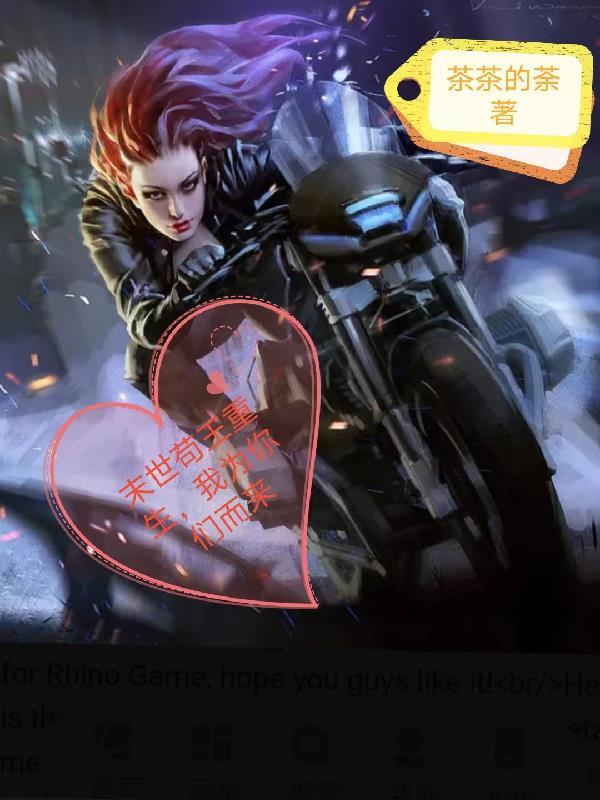富士小说>将军要娶妻 > 第181章 赤沙筑城折柳成亭(第1页)
第181章 赤沙筑城折柳成亭(第1页)
西域的风沙仿佛永不知疲倦,日复一日地舔舐着萧楚城新筑的土墙,将粗粝的表面打磨得愈光滑,也染上了一层更深沉的赭黄。营地里却渐渐有了些不一样的气息。引水渠旁开垦出的几畦菜地,稀稀拉拉地冒出了倔强的嫩绿;简陋的窝棚间,多了几缕炊烟,混合着烤饼和炖煮羊肉的粗粝香气;孩童们追逐嬉闹的尖叫声,偶尔也能压过风沙的呜咽。
然而,营地中央那座最“坚固”的棚屋内,沉疴的气息依旧浓重得化不开。
楚明昭靠坐在铺着厚厚干草和洁净粗布的矮榻上,身上裹着一件半旧的靛青色棉袍——那是林红缨用自己的旧衣改制的,宽大的袍袖越衬得她形销骨立。深陷在青黑色眼窝中的眸子半阖着,目光涣散地落在对面土墙上被风沙侵蚀出的、如同鬼斧神工般的天然纹路上。每一次呼吸依旧带着胸腔深处沉闷的杂音,如同破旧风箱的叹息,牵动着左胸致命的箭创,带来阵阵绵长而顽固的钝痛。
那只包裹着白麻布的右手,安静地搁在膝上。掌心的烙印在药膏的覆盖下,痛楚已从尖锐转为一种沉闷的、如同烙印在骨子里的钝感。枕边,那半截被粗布包裹的青铜残刃,依旧如同一个沉默的、冰冷的坐标,静静地躺在触手可及之处。
林红缨端着一碗刚熬好的、散着浓烈药草苦涩气息的汤药,小心翼翼地坐到榻边。她动作极轻,用木勺舀起一勺深褐色的药汁,吹了吹,递到楚明昭干裂的唇边。
“殿下,该用药了。”她的声音压得极低,带着一种习以为常的、沉重的温柔。
楚明昭涣散的目光极其缓慢地从墙上的纹路移开,落在冒着热气的药勺上。浓烈的苦涩气味钻入鼻腔,让她本就紧蹙的眉心拧得更深。她沾着药渍的唇极其微弱地翕动了一下,似乎想抗拒,最终还是极其艰难地、顺从地微微张开了口。
温热的药汁滑过灼痛的喉咙,带来熟悉的苦涩。每一口吞咽都伴随着肺腑深处的滞涩感,让她纤细的脖颈微微颤抖。林红缨耐心地一勺一勺喂着,目光却不由自主地落在楚明昭那只包裹着白麻布的手上。那手的指尖,无意识地蜷缩着,轻轻抠着棉袍粗糙的布料,留下几道细微的褶皱。
一碗药终于见底。林红缨放下碗,拿起一块干净的湿布巾,极其轻柔地擦拭楚明昭唇边的药渍。就在布巾拂过她苍白消瘦的下颌时——
“叮…咚……”
一声极其细微、却异常清晰的乐音,如同沙漠深处一滴清泉坠落玉盘,穿透了棚屋厚实的土墙和弥漫的药味,极其微弱地飘了进来!
那声音清越、空灵,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穿透力和孤寂感,仿佛能直接叩击在灵魂最深处!
楚明昭深陷在青黑色眼窝中的眸子,在听到这缕乐音的瞬间,猛地剧烈一颤!布满了蛛网般血丝的瞳孔骤然收缩!涣散的目光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巨力强行凝聚!她的身体如同被无形的电流击中,极其轻微地、却无法抑制地向上挺直了一瞬!搁在膝上的那只包裹着白麻布的右手,指关节猛地蜷紧,死死抠住了粗糙的棉袍布料!
“呃……”一声极其压抑的、如同受伤小兽般的呜咽,从她紧抿的唇齿间溢出。肺腑深处撕裂般的钝痛被这突如其来的乐音狠狠搅动,额角瞬间渗出细密的冷汗!
“殿下?”林红缨被她的反应吓了一跳,手中的布巾掉落在地。
楚明昭没有回应。她的头极其艰难地、无意识地微微侧向一边,那只完好无损的左耳,似乎在极力捕捉着风中那缕若有若无、断断续续的乐音。深陷的眼窝中,翻涌着巨大的惊愕、难以置信,以及一种深入骨髓的、被强行唤醒的剧痛!
这旋律……是《折柳》!
是她前世在无数个孤灯长明的深夜,在讲武堂空旷的校场上,在边关萧瑟的月色下,用一管随手削制的竹笛,吹奏出的、寄托了无尽乡愁与孤寂的曲子!是她亲手所作!只属于她一个人的……《折柳》!
怎么会……在这里?!
“是……城主……”林红缨看着楚明昭的反应,瞬间明白了那乐音的来源,声音带着一丝复杂和低沉的叹息,“在……‘折柳亭’……”
折柳亭?
楚明昭涣散的瞳孔剧烈地收缩着,巨大的眩晕感和撕裂般的痛楚让她眼前阵阵黑。她沾满冷汗的左手死死抓住身下的粗布,指关节因用力而泛出青白色,仿佛在与体内翻江倒海的剧痛和那猝不及防闯入灵魂的故曲对抗。
---
萧楚城新筑的土墙,在营地西侧拐角处,向外延伸出了一小段凸出的平台。平台不大,仅能容纳数人立足。此刻,平台之上,矗立着一座极其简陋、却吸引了整个营地目光的小小建筑。
那甚至不能称之为“亭”。它没有雕梁画栋,没有飞檐斗拱。仅仅是用几根新砍伐的、尚未完全干透的粗壮胡杨木做柱子,顶端交叉架起几根稍细的横梁,上面覆盖着一层用新鲜芦苇和粗麻绳紧密编织成的、勉强能遮阳挡沙的简陋顶棚。四面无墙,只有稀疏的几根木栏象征性地围了一下。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
这便是“折柳亭”。
亭子的建造,并非萧凛下令。那日商队离开后,巴图尔和几个曾在边军待过、粗通木工的老卒,看着城主每日拖着伤躯,沉默地登上那段新筑的土墙,面朝东方无尽沙海一站便是几个时辰的背影,心中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酸涩与崇敬便再也按捺不住。
“城主心里苦!”巴图尔蹲在墙角,用粗糙的大手搓着一根胡杨木棍,声音闷闷的,“建个亭子吧!好歹……好歹能遮遮日头风沙!”
流民们沉默地响应了。有力气的汉子扛来木头,妇人们采集坚韧的芦苇编织顶棚,连孩童们都帮着搬运捆扎用的草绳。没有图纸,没有监工,全凭一股心照不宣的默契和对那道沉默身影的敬畏。短短几日,这座简陋到近乎寒酸的小亭便悄然立在了土墙之上,成了萧楚城这座沙海孤城中,一道突兀却又无比和谐的风景。
此刻,夕阳如同一个巨大的、熔化的金球,沉沉地坠向西边沙海的地平线。万丈霞光泼洒下来,将整片天地染成一片辉煌而悲壮的赤金色。土墙、沙丘、稀疏的胡杨林,乃至营地简陋的窝棚,都披上了一层流动的金纱。
折柳亭内,萧凛高大的身影背对着营地,面朝东方。他依旧戴着那张冰冷光滑的青铜面具,遮住了所有表情。身上那件半旧的靛青色粗布长衫在晚风中微微拂动,勾勒出宽厚而略显孤寂的肩背轮廓。他沾着沙尘、骨节分明的大手,正握着一支同样简陋、显然是用新竹削制的粗糙短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