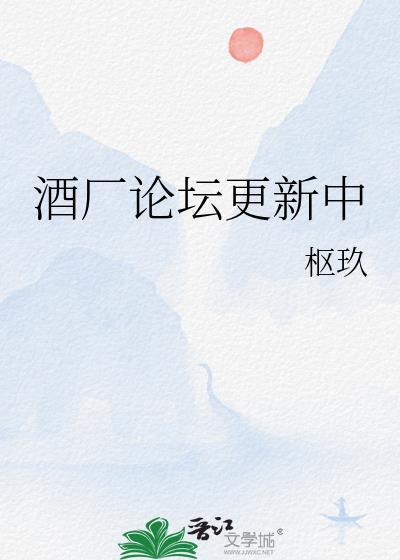富士小说>君妇升职手札最新章节更新更新内容 > 190200(第10页)
190200(第10页)
元嘉猛地睁开眼,抓过手边的杯盏便狠狠掼在地上。瓷片四溅,滚热的茶水泼洒开来,直惊得头前几名官员连连后退,吵嚷声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谁敢妄加揣测圣意!谁敢污蔑予!”
元嘉霍然起身,眼底挟着滔天怒火,声音陡然拔高,“诸位质问予之前,不妨先告诉予,究竟是从何处听来的风言风语,张口便敢称一个面都没见过的人为‘名医’?若依尔等所言,今次随同陛下出行的太医、多年来尽心侍奉在宫里的医官们,岂非都是些昏庸无能之辈?!”
她胸口剧烈起伏着,声音因愤怒而微微发颤,“那不过是个神志不清的疯癫僧人,竟敢妄言在陛下身上动刀放血……若有差池,尔等谁担待得起!陛下万金之躯,你们竟敢拿他的性命去赌一个疯子的胡言乱语,简直本末倒置!予倒想问问你们,究竟存的是什么心思!”
元嘉重重喘了口气,目光如利刃般从每一个人脸上扫过,“予下令将其关押,正是为了陛下安危、江山社稷着想!尔等身为陛下倚重的股肱之臣,不思及如何尽忠竭节,反以此等诛心之论构陷中宫,当真是胆大包天哪!”
屋内一时寂静无声,众人被元嘉的话震慑在原地,竟无人敢再轻易开口。
元嘉略一停顿,目光平静地扫过眼前噤若寒蝉的一众官员,最终将视线停留在立于最前方的端王身上——方才正是他说出了“不臣之心”四个字。
“端王爷,”她唤着端王的封号,语气平淡得令人胆寒,“予可是何处惹了你不满,还是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竟叫你以‘不臣之心’四个字质问于予。”
端王一时语塞,“这……”
“答不出来?”元嘉向前走了两步,“那予便换个问题吧……敢问端王爷,陛下病重垂危这两日,你在何处?”
这一次,不待端王作答,元嘉便骤然冷下声音,“王爷急着替陛下体察民情,去了十里开外的平乐乡,硬拉了娄家郎君作陪,在那里喝酒听曲,寻欢作乐,好不惬意!一直到昨日深夜方才尽兴归来,只怕连陛下的病况都未曾探明,今日就敢站在这里,和他们一起来逼问予了!”
元嘉每说一句,便向前逼近一步,端王的脸色便白上一分。等到元嘉彻底站定在端王面前时,他的额角更渗出了细密的冷汗。
“王爷今日作为,究竟是真的为陛下考虑,还是……”元嘉语气陡然转厉,“做这亲王做腻味了,想趁着陛下病重之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亦或是……与谁暗中勾连,存了要帮扶他的心思?!”
端王被元嘉这一连串的话刺得面红耳赤,不自觉退后半步,脱口道:“臣绝无此意,是……”话才说到一半,便猛地扭头朝身后某个方向怒吼起来,“你不是说——”
却又一下子戛然而止,显然是意识到了自己失言,遂干脆闭紧了嘴。
元嘉顺着他视线的方向望去,只见尽头那处站了好几个埋着脑袋、不言不语的官员,一时竟难以分辨前者的话究竟在指责谁。但如此看来,这位端王爷大抵是被谁当成出头鸟使了。
元嘉心下稍安,如无必要,她也不想在这关头和这群皇室宗亲们闹僵,毕竟……之后还有要他们帮腔执言的地方。
但也不能轻易放过。
思及此,元嘉当即哼笑一声,语带讥讽道:“原以为端王爷这些年来总算有了些长进,当差虽无大功,倒也勉勉强强,隐约能瞧出几分先帝当年的影子。可如今看来,却是陛下和予都高估了王爷。”
“王爷是陛下兄长,予原还指望着王爷能在这当头帮衬一二,”元嘉一脸的痛心疾首,“却是不添乱便不错了……唉,早知道王爷如此分不清是非好歹,予当初便该让你那位贤淑的王妃一同随行!离了端王妃在身边提点,王爷这耳朵便跟聋了一般,眼睛也是瞎的,连人话都听不明白了!”
一番话极尽羞辱之能事,直将端王气得浑身发抖,却碍于皇后威势,不敢当场反驳,只能铁青着脸低下头去。
正当时,燕景璇疾步走进屋内。为稳妥起见,她先去察看了一番那和尚的情况,是以迟来了片刻,进来时恰好将元嘉与端王的这番争执听在耳里,当即沉了脸色,径直走到端王面前,在众人惊愕的注视下,扬手狠狠掴了前者一巴掌。
“啪!”
这一下力道显然极重,直将猝不及防的端王打得头都偏了过去,脸上瞬间浮出红痕。
“……皇姊?!”
端王踉跄两步站稳,半捂着脸,一副不敢置信的模样。
“混账东西!”
燕景璇怒容满面,指着端王厉声斥道:“这一巴掌,是替皇后殿下打的!陛下病重,皇后日夜忧心、殚精竭虑,你身为宗亲重臣,不思为陛下、皇后分忧,反倒听信些无边谣言,在这里大放厥词,以下犯上!是真拿自己当金贵人了呀!本宫打你,就是要让你清醒清醒!究竟是谁给你的胆子,敢对皇后如此不敬!”
燕景璇见端王因她的话面色铁青,嘴唇哆嗦却不敢言,便知这人正为自己大庭广众之下跌了面子而恼恨,当即冷笑一声,语锋更利,“怎么?本宫这个当姊姊的,还教训不得你这个弟弟了吗!”
说着,反手又掴了人一巴掌。
“这一巴掌,”燕景璇没有再向近在咫尺的端王分去一丝余光,只冷冷盯着屋内鸦雀无声的一众官员们,“是打你目无尊上,狂悖无状!记住了,记清楚了,是本宫这个做姊姊的,打的你!”
燕景璇此举,除为了向所有人表明自己的立场外,更替元嘉做了因皇后身份而不能亲为之事。而这接连打在端王脸上的两巴掌,不仅将前者的气焰灭了个彻底,更是起杀鸡儆猴之效,让所有蠢蠢欲动的官员齐齐噤声,又冷汗涔涔地低下头去,再不敢与元嘉和燕景璇凌厉的目光对视。
见状,元嘉朝燕景璇递去一个眼神,前者立刻会意,冷哼一声,便振袖退回到元嘉身侧。一直静立在元嘉身后的逢春随即上前半步,面向众臣,声音清越平稳,语调不高不低,却再清晰不过地传到所有人耳里——
“诸位大人若真心欲为陛下分忧,太医们眼下就在隔壁屋舍斟酌新方,可有谁去关心过进展?距往上京快马急报也已好几日,又有谁去督看过有无回信?若心系龙体,奴婢亦可为大人们指一条明路,去陛下屋子外静心守候,也算是表了忠心。”
她神色平静地扫过表情不一的众人,语气依旧不卑不亢,“又或者……学着太子殿下的模样,跪在三清祖师面前诵经祈福,以尽臣子本分。”
逢春顿了顿,声音陡然沉了下去,“无论何种方式,都好过将皇后殿下围堵在此,徒作无谓争执。此举非但有犯上僭越之嫌,更徒耗光阴,于陛下病情无半分益处……诸位大人,请自便!”
一番话说得条理分明,温和却不失强硬,竟叫人一时忘了逢春的宫女身份,只觉那话中的分量与威压不亚于皇后谕令。
底下人左右相觑,表情讪讪,早前兴师问罪的气势荡然无存。正犹豫间,见最前头的端王已然捂着红肿的脸,大跨步转身离开,便也灰溜溜地拱手行礼,一个个如潮水般退散,顷刻间便走了个干净——
作者有话说:也算是打戏了吧[菜狗]
第200章作何选皇姊以为,陛下如今……还有的……
眼见屋内重新变得空荡荡的,燕景璇这才几不可察地松了口气,她看向元嘉,神情颇为懊恼,“早知他们会干出这样的事,我便不该先去瞧了那和尚的好赖,就该直接来您这儿守着……万幸,总算没误了事,来得还不算太迟。”
她略一停顿,眼中掠过一丝狠厉,“那和尚疯癫至此,咱们不能再留了,我这就去找人处理干净。”
元嘉却摇了头,道:“杀他容易,但若陛下醒过来后又要见他,我们再去哪里找个一模一样的顶上?”
燕景璇愈发气恼,十指深陷进掌心,恨声道:“都是我的过错,挑来挑去,竟选中这么个疯癫误事的!还有那些伺候的奴才,舌头都不必留了,竟敢将榻前之事轻易泄露给外臣,简直该杀!”
“……噢?”元嘉淡淡瞥她一眼,“那皇姊怕不是要先去将陛下身边的申时安和兰华给处置了,毕竟那也是伺候陛下的奴才。”
如同被当头浇下一盆冷水,燕景璇顿时语塞。她当然知道动不得那些御前心腹,她也没这个本事和胆量,可自己气头上的迁怒之语就这样被元嘉毫不客气地点破,面上难免挂不住,当即绷紧了脸,抿嘴不语。
屋内气氛一时凝滞。
元嘉对燕景璇这反应早已司空见惯,深知她这脾气来的快,去的也快,并非是真心计较,故而也不去哄劝,只兀自垂眸深思了片刻,便将这小小不快揭了过去,转而问起另一桩事来,“你过来时,瞧见阿昱了没?他是不是……又跑去正殿诵经了?”
燕景璇虽还因方才之事尚存余愠,但闻言仍回过头看着元嘉,又替燕明昱解释起来——
“如今这观里乱糟糟的,他一个半大小子,去哪里不是添乱?守在祁弟榻前徒增伤悲,面对外臣又手足无措,倒不如让他遂着自己的心意,去三清祖师面前祝祷祈愿,既全了孝心,也能寻个寄托,得片刻安慰……我觉得,情有可原。”
![暴君的炮灰男后[穿书]](/img/172907.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