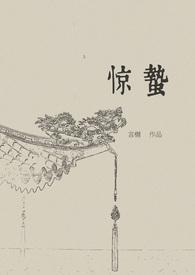富士小说>七日约ⅱ全本 > 番外2(第3页)
番外2(第3页)
然後并拢琴弓,优雅行礼,对明月说:“您好,我是涅盘的首席文森特,很高兴认识你。”
又用俄语说‘再见,朋友,不必握手诀别’,声音像倒放的音频。
托文森特的福,这是明昕能听懂的唯一一句俄语,她後来在网上查过,出自叶塞宁的《诀别诗》,非常经典。
先说你好,再说道别,也不管对方有没有听懂,文森特再次优雅行礼,捧着空空如也的托盘退下了。
很快,除了他们这桌,这场闹剧不再有人记得。
等文森特的身影完全消失不见,明昕伸了个懒腰。
“他应该去换衣服了,”明昕说,“我也差不多该走了。”
明月依旧维持着先前的坐姿,十指交叉,用复杂的目光凝视着眼前自己从小看到大的妹妹。
这些年明父退位,将自家公司的全部生意全权交给明月代理,而他也不负所托,以雷霆手腕亲自操持,让家里的资産翻了两倍不止。
他掌控公司,掌控人脉,唯独不知道他最疼爱的妹妹,是什麽时候脱离了他的掌心。
“原来你喜欢这种类型,”明月的声音比平时低沉三分,“漂泊不定,没有根基。”
对面的明昕却笑了下:“其实从见到他第一面开始,我就知道他会走。”
明月说:“然後呢?”
“然後,他为我回来了。”
明昕摩挲着指根的戒指,钻石切割精良,刺得明月眼睛生疼,让他不由得颦起眉毛。
“所以你就要为了这个‘回来’,接受他这麽敷衍的求婚?用侍应生的托盘?”
“不不不,不是这回事。”
嘴角勾起一个小小的弧度,自家妹妹向来蕴着水光的眸子被笑意填满了。
“戒指戴了可以摘,婚约定了可以毁,一枚戒指而已,代表不了什麽。哥,我愿意接受他,主要是因为祁芳。”
听到久违的名字,明月神色微微动容。
明昕继续说:“细节就不说了,不然得讲十四万字,总之我相信我的判断,我也相信我有能力保护好自己。”
从提到祁芳的名字起,明月就不说话了,只定定看着明昕的眼睛。
半晌,他长长叹息了声,像明昕很小时候那样,伸手拍了拍她的头。
“你长大了。”明月说,表情复杂。
明昕欣然接受。
喝掉杯里最後一口红酒,明昕站起身,马上有侍应过来,从衣架上摘下外套。
“祁芳的祭日也快到了,下周一,对吧,”明月依旧坐在原地,“今年我可能会有点忙,你空了替我去看她。”
明昕心里一动,忍不住开口:“哥,你是不是——”知道祁芳曾经喜欢你。
她没说完,只见金丝镜片後的那双狭长眼睛微微弯起一点,很轻地摇头。
意思已经很明确了,是个‘你不要问’。
走出旋转门,蓝城华灯初上。
气温比出来的时候转冷了不少,文森特正等在外面,已经换回了正常的服装,烟灰色的呢子大衣。
男人从怀里掏出一团驼色围巾,献宝似的凑到明昕身边。
“天气预报说今晚降温,所以我带了这个。”
明昕没接,而是略略伸出脖子。
喀什米尔的柔软布料被捂得温热,颈间混着文森特的体温,心上也萦着层层的暖意。
任由对方给系围巾,稍显亲昵的距离,明昕得以近距离打量眼前这幅皮囊,那麽好看,无数次害她一见钟情。
蓝城的夜景灯红酒绿,他半张脸沉在黑暗里,半张脸浸着路灯特有的柔光,细细将她肩上的围巾展平,神情专注,就好像这世上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大事。
都说人生若只如初见,可初遇那天,我可曾设想过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