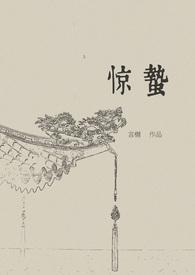富士小说>七日约ⅱ全本 > 番外2(第4页)
番外2(第4页)
明昕忽而笑了下。
“怎麽?”
文森特本想後退半步,回到安全的社交距离,却被明昕用三指扯住领口。
“我哥说,他快结婚了,”明昕喃喃道,“和一个他根本不爱,也几乎没怎麽见过面的人。”
太近了,明昕应该是喝了酒,呼吸里有股甜腻的气息,葡萄酒,也许还喝了开场的香槟。
这股味道混合着她身上的甜香,在他身上烘起把燎原的火,文森特屏息,衷心祈祷自己的耳根不要红得太快。
“可以理解,”他艰难开口,“婚姻无外乎三种,因为感情,因为利益,或者二者得兼。”
明昕却摇摇头:“我想说的不是这个,虽然我不知道这位未来的嫂子是谁家的千金,但是啊,我看我准嫂子的那张照片,她的神态有那麽一点像祁芳。”
她阖上眼睫,接下来的几秒钟无人说话,只有跑车的引擎由远及近,又嗡地一声飞速远去。
“涅盘有次在金城组局,我请一名偶遇的粉丝喝了杯粉红佳人,”文森特突然开口,“只因为我听到她打电话,声音有一点像你。”
明昕没把话说得很明白,可文森特都懂。
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就算幼时长于苦难,却也没有被世俗打磨成无趣的碌碌庸人,始终怀揣着赤子般的敏锐心思,行过万千国度,听遍诡谲奇闻,一边懂礼节知进退,一边是近乎不谙世事的天真。
是她的基因本能,和她的自我意识,共同挑选出的人。
她想,她不该喝掉最後一口红酒。
不然也不会有某个念头跳出来。
——不要再逗他了吧,毕竟没有哪条规定写着,必须由男方主动才符合法律。
她踮起脚,拽着他衣领的三指微微使力。
周遭明明极为嘈杂,却又在那个瞬间缄默,化为一片靡靡的丶并不重要的背景音。
先是冰冷僵硬,又很快滚烫鲜活。
风纪扣不堪重负地崩开些许,唇微分,文森特马上反客为主,修长手指揽过後颈,重新欺上来。
她盘在後脑的卷发散了,有风一吹,将二人圈进栗色的森林。
不再有手指的阻碍,他的气息轰然撞进她肺里,犹如斯德洛格郊外那清澈见底的湖水,层层裹挟,层层沉溺。
吻毕,明昕脚跟着地,悄悄蜷起踮得酸麻的脚趾。
文森特眼角微红,手背擦过唇瓣,怯怯看她一眼,像个後知後觉做了错事的小孩。
他不住舔着下唇,控诉道:“顺序错了,我还没征得你的原谅,让你对我重新燃起兴趣。”
是了,自从文森特把他那一行李箱的过去拿进Loft,就被明昕丢到了角落里,一次都没有翻看过。
她不是不好奇,她只是更想听文森特自己说。
结果却被文森特误会成她对他不感兴趣。
不对,这不是重点,重点是——
“我们什麽时候顺序正确过?”明昕给他掰手指,“正常人先相识,再相知,交往了才考虑求婚,分离前才会彼此道别,我们呢?什麽时候正常过?”
文森特马上被她说服了,点头称是,又说:“再亲一下好不好。”
明昕摇头:“你不用询问我的意见。”
于是他们再次在蓝城大厦的正门口接吻,在这座城市的正中心。
像两颗相邻的尘埃,被芸芸衆生湮没。
活在童话故事里的魔术师连接吻也很笨拙,因为他不知道外面是什麽样的。
毕竟童话故事只会收尾在‘从此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未来被作者一笔带过。
好在他的学习能力不错,很快掌握了技巧。
然後,他就被从故事中解脱,走出童话,走进现实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