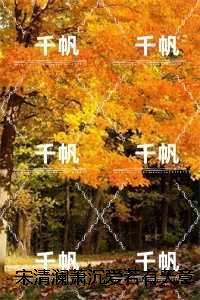富士小说>折花枝的 > 6070(第14页)
6070(第14页)
人家姑娘见她已然呆滞,便轻手轻脚为她洗脸更衣,一圈观察下来,小医徒舒了口气,“还好,淤青是不少,但并无大碍。我给你开点活血化瘀的药。”小医徒替她拨开凌乱的发髻,轻声细语道,“姑娘,你定是吓傻了吧?你一个人把他推过来,真是不容易。不过不用怕了,我们这儿很安全的。”
她温柔细语,令李沐妍的警戒悄然消散。小医徒抹了点金疮药,擦涂她磨破了皮的手掌。“姑娘,你别难过,先在我屋里睡一觉吧。我呀,每次被师傅骂,就回屋睡大觉。只要睡上一个饱觉,就能忘记所有的烦心事。”
“真的吗……真的睡一觉就能忘记吗?”
小医徒嘻嘻一笑,“当然了!放心,那个大叔我们会照看好的,你就先睡一会儿吧。等第二天醒了,就又是高高兴兴的一天了。”
李沐妍觉得自己像一只流浪的小猫,被人捡了回来,暖暖地捂在了怀里。小医徒扶她躺下,她一沾到那帛枕,便沉沉地睡去了。
她做了个梦,梦里头下了好大的一场雪,即便是宁王府的参月台也都被埋进了积雪里……所有的一切,都埋进了雪里,随着她沉睡的呼吸,一点点散去……
第二日,当她终于睡醒睁开眼时,所有旧事都已离她而去。她慵懒地打了个哈欠,环顾四周,发现自己身处一间陌生的屋子里。
一时之间,她好生恍惚:我是谁?我在哪儿?
第70章你是我的妻子
瑞香与春华日夜兼程,总算赶到了春猎的行宫,可她们被拦了下来,只得静候通报。
时过黄昏,宵月赶早高挂,萧灼正与温靖荷在河边漫步。
温靖荷提着裙摆来他身后,欣喜道,“王爷您看,今晚的月色何其明亮。”
昨日萧灼与皇上不欢而散,但皇上仍执意赐婚。此刻他无心抬头,平淡应之,“是啊。”
温靖荷两颊扑红,这是她头一回离他这般近。“其实此次能随家父出行,我已知足。没想到圣上竟还许了我们的婚事。王爷可还记得?我年十六时,同祖父入宫赴宴,与诸姊殿上献艺。我弹琴出了纰漏,众人皆笑话我时,唯有王爷您挺身而出,为我解围。自那以后,我便决定,此生非君不嫁。我们……”
萧灼打断其言,神色凝重道,“温小姐,有句话本王今日必须同你说清楚。”
温靖荷愣生愕然,一向这种开头都不会是好事。“您请说。”
“本王如今孑然一身,并无成婚之意。温小姐你才貌双全,必能找到更适合的良配。别在本王身上……”
“可我已经说了……”她攥紧了帕子,声音微颤,“没关系,反正都这么多年了,我也不急于一时。只要王爷您心有靖荷,就是再等个三年五年,我也愿意。”
“别等我。于你,我不会是一个好丈夫的。”
“为什么?”
“我是你的非君不嫁,但你不是我的非卿不娶。你应该找一个唯你不可的人相伴终生。你我若是强求,得来终是苦果。”
温靖荷急切地拉住他的衣袖,“请您不要说这么绝情的话,你我不试怎知……”
可说话间,从行宫门口赶来的杨从武前来禀报,“报告王爷,瑞香和春华来了,她们说……”他凑到萧灼耳旁低语,“李沐妍不见了,生死未卜……”
“什么?!”
连温靖荷都能看出萧灼眼中的惊慌失措。
“带我去见她们!”他无暇顾及温靖荷,跟着杨从武一同离开了此处。
在瑞香和春华口中,他得知了事情的经过,眼下第一要务就是回王都找人。他遂跨上宝驹,遣人去向皇上禀报,“告诉圣上,臣弟有要事,不能相陪了!圣上要臣弟做的事,臣弟做不到。要罚要骂,等圣上回宫,悉听尊便!”
言罢,他率宁王府众人,策马如飞,一路往王都赶回……
——
李沐妍迷蒙苏醒,悠然从肺底舒出一口气来,如同任督二脉贯通,好不畅快。她不知自己所在何处?她甚至自己连姓甚名谁都想不起来。但不知怎的,她一点儿也不慌张,反而是异常的轻惬。
步出屋门,恰见一姑娘前来招呼,“你醒啦!再不醒我就得进屋救你了,你可知你足足睡了十二个时辰!”
李沐妍双眸茫然,“我……你认识我?我怎么了?怎会睡这么久呀?”
那姑娘看她双眼懵懂,便觉事情不对,急道,“姑娘,你可别吓我!”她放下药篮,摸了摸她的额头,不似是发烧了。
小医徒焦急万分。李沐妍却犹在傻乐,“我可能是出了岔子,我连我自己是谁都想不起来了。”
……
医馆师傅对她一顿检查,最终得下结论,“为师知道,有时人若遭逢巨变,便会失去记忆。”
“巨变?”李沐妍无论如何也记不得那是何等的巨变?她只顾问,“那我是不是永远也想不起来了?”
师傅把了把胡须言,“这也未必。有人一辈子也想不起来,有人却能在数日内恢复。姑娘你不妨回家去,说不定触景生情便能有所忆起。”
小医徒忙不迭笑了,“师傅,人家都失忆了,哪还记得家呀?”
“哦,对哦!哈哈哈!”师傅抓耳挠腮,惭愧憨笑。
沐妍见二人乐呵,亦随之而笑,至此还未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对啦!”小医徒灵光一现,“和你一起的那大叔或许知道一些?!”
“大叔?我还有叔?!”李沐妍两眼放光,紧赶着去见了大叔。
那大叔卧在病榻上,气息奄奄将所知一切具告,最后奉劝她说,“姑娘,我只知你乃宁王府的人,但你可千万别再回去了。你现在还失忆了,只怕一踏入皇城就要遭殃!”
“原来如此,我是宁王府的人……”可李沐妍依旧摸不着头脑。
小医徒也帮着分析,“我猜你应该身份不凡。你可知你出手有多阔绰?付钱时,直接给了我一支金簪子!”小医徒将金簪拿来,续道,“这等手艺的簪子,我平生见都未曾见过。又是宝珠又是真金的,不得值个几十上百两?你若只是王府的下人,怎用得起这样的首饰?”
“那我能是谁?那那个宁王又是谁?”
已完结热门小说推荐
- 宋清澜萧沉爱若有天意,兜转终可回:结局+番外宋清澜萧沉
- 原来当年出卖父亲的人竟然不是陆风,而是为父亲讨回公道的萧沉。那具被折磨得面目全非的遗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