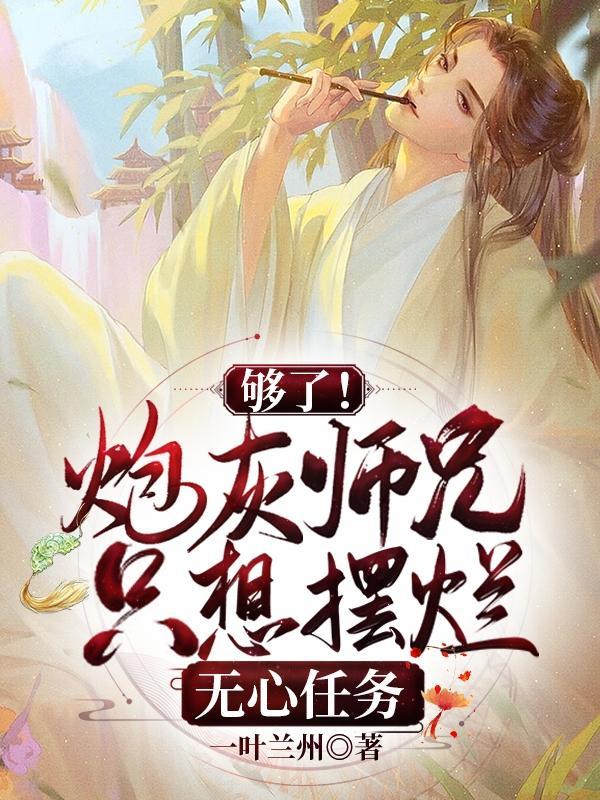富士小说>汴京调色手札免费 > 第 110 章(第2页)
第 110 章(第2页)
她定了定心,说起後续的发现来,“登记在册的两百七十八名工匠,那天统共抓了一百五十名,尚有一百二十八名不见人。我事後又仔细对比了百工册,这些人多数是记在绫锦院名下。绫锦院有自个的染坊丶织院,你说那些人会藏在这里头吗?”
韩雨钟觉得有很道理,“有可能,他们进京後怎样都需要一个落脚地。哪怕之後散入汴京,也会留有不少痕迹。”
既然他同意,骆抒提出去绫锦院看看,韩雨钟便与她同去。
绫锦院地处昭庆坊,院子里摆着几百架织机,工匠们穿梭其中,手中的木梭一刻不停。这一眼扫过去,零零散散工匠加兵士约有几百号人。若想要藏下一百号人,是很轻松的。
韩雨钟叫来管事,问道:“先前为南郊大礼征集的工匠,依照旧例把人安置在哪里?”
管事正叫苦呢,两日前礼部把人喊走说是学什麽样式,後来又说抓了不少工匠,好些都是绫锦院的。吓得他赶紧召集人一查,分明一个也没少嘛。
本想把此事说与上官柳少监,结果去了几次少府监也没见到人,只好回来忙活了。
承郡王这麽一问,他只能老实回答,“都是安置在附近的民巷中。”
“前面带路。”
一行人又去了这附近的民巷,的确好些工匠都住在这里。门上墙上地上都有染料残留,骆抒能看出来。
管事介绍,“这里统共有三十四间房,按每两人一间,总计住了六十八个人。”
他又补了一句,“这六十八个人都在,王爷要见见他们吗?”
心里却嘀咕,怎麽天潢贵胄还跟工匠较上劲了。
韩雨钟点头,“叫他们来。”
很快,绫锦院这六十八个人全被叫到民巷中,每个人挨个认了自己的房间丶床铺,面上看着都没有什麽问题。
管事正为自己过关了窃喜,却听韩雨钟问,“礼部百工册上可是记着,你们绫锦院名下不止六十八名工匠,其他的去哪儿了?”
他额角顿时激出冷汗,原来是为了此事!怪不得柳少监不见了,想来承郡王已全部查明,他哆哆嗦嗦回道:“王爷明鉴,小人也只是听上官吩咐,是柳少监想要加人进来吃空饷,这钱全进了他的腰包,小人一分没拿。”
韩雨钟气不打一处来,就连工匠这点蝇头小利他们也要贪。
“也就说,你没有见过多出来的人?”
管事头摇得像拨浪鼓,“没有没有,全都是柳少监管的。”
骆抒问工匠们,“你们呢,可曾见过生人?”
其馀工匠也是一脸糊涂,他们望了望彼此,纷纷回答,“没有见过。”
骆抒皱眉,难道他们从没来过?自己是猜错了。
她又细问,“你们是何时住进来的?”
“七日前。”
七日?骆抒赶紧翻了翻百工册,上面分明注明了工匠们是九日前进京的。
“我想进你们的屋子看看。”
她如今已经很有气势,又有王爷作陪,等闲人不敢与她平视和说话,只讷讷点头。
骆抒开始在屋子里搜寻起来,那些兵士会在这里住了两日吗?那之後又去了哪里?汴京城五人一保,左邻右舍都认识,平日里出现一个生人都会引起别人警觉。除了没人敢查的皇家工坊,还能藏在哪儿呢。
这些屋子都是一个制式。青砖石瓦,屋子里靠墙各放了两张床,中间一个木桌隔开,木桌上方就是窗棂,外头又是一处民巷的後门。
骆抒拉出窗户,往外探去,四周安安静静,只能听到院里染织的声音。
突然间,她福至心灵,朝管事问道:“登记在册的工匠们,有没有每日做活的定量,可有必须完成多少的说法,有没有册子,拿过来给我看看。”
管事说有,“每个人快慢不一,倒没有勒令他们每日必须做多少,但册子是有的。”
他拿出册子,好些工匠尚不明白是何用意,以为是贵人不满意他们的手艺,垂下头去准备听训。但骆抒注意到,有几人垂得慢些,脑袋伸长了,想往她手上的册子看。
她刚才也是突然想到,谁规定了这些兵士一定全都是人高马大的,他们就不能僞装得和寻常工匠一样,老老实实地干活吗?
且她看了好几间屋子,有些人住得久了添置了许多杂物,但有的始终只有床铺灯烛,别的一点也没有,更验证了她的猜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