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小说>制霸的意思是什么 > 第546章 爸我好想你(第1页)
第546章 爸我好想你(第1页)
突然,吴小雨的身体微微一颤,她指着墙基处,轻声说道:“这里……有东西……在流动……”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个颤抖的声音:“那年……他也是这样说的……他说……墙在喘……”
于佳佳转过身,看到赵志忠老人拄着拐杖,站在不远处,浑浊的眼睛里充满了震惊和恐惧。
当晚,赵志忠老人颤颤巍巍地将一个沉重的包裹交到了于佳佳手中。
打开一看,是三十七册厚厚的日志本,纸张已经泛黄,字迹也有些模糊,但每一个字,都记录着赵志忠老人十二年的坚守。
从年到年,每日凌晨三点,赵志忠老人都会准时出现在老城区的地下管网,用他的耳朵,用他的眼睛,用他的笔,记录着每一个井盖的微震,每一寸地温的变化,每一丝水流的声调。
于佳佳捧着这些日志,仿佛捧着一段被时间尘封的历史。
她意识到,这些日志,是打破“经验非科学”偏见的关键证据,但如果公开,很可能会引对当年决策层的政治追责。
“这可真是个烫手的山芋啊……”于佳佳揉了揉眉心,感到一阵头疼。
她找到了陈砚田,市规划院的副总工,一个理性中带有人文挣扎的潜在盟友。
“老陈,帮我个忙。”她把赵志忠的日志交给了陈砚田,并把自己面临的困境告诉了他。
陈砚田仔细地翻阅着那些日志,眉头越皱越紧。
他沉默了很久,最终抬起头,看着于佳佳,说道:“我们可以试试……以‘历史气候数据对照研究’的名义,向市科委申报一个课题。”
于佳佳眼睛一亮:“把这些敏感内容,转化为学术话语?”
“没错。”陈砚田点了点头,“这样,既可以保护赵老,又可以把这些珍贵的资料公之于众。”
吴小雨也加入了他们的计划。
她利用自己的感官联觉能力,将三十年来的震动频率,与城市生的重大事件并置——地铁开工、房价跃升、广场改造……
每一轮剧烈的波动后,都有赵工兄弟标记的“镇压层”。
一幅名为“声纹年轮图”的巨型图谱,正在慢慢成型。
就在一切准备就绪,即将提交申报的前夕,档案馆突然通知于佳佳,说赵志忠的日志原件需要“例行消毒封存”。
于佳佳心里咯噔一下
“小波,小满,快!”她连夜组织团队,对所有日志进行抢救性扫描。
姚小波用暗光摄影翻拍手稿,林小满则将关键的声纹转译为可听化的音频。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气氛紧张得令人窒息。
最后一册日志刚刚扫描完毕,两名穿着制服的人员就敲响了于佳佳的办公室的门。
“我们是档案馆的,奉命来接管材料。”其中一人面无表情地说道。
于佳佳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保持冷静:“不好意思,这些日志是私人资料,不能交给你们。”
“这是上面的命令,请你配合。”对方语气强硬,似乎不容置疑。
就在这时,楼道里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声音。
“你们要干什么?!”
“不许拿走!”
“这是赵工的命根子!”
于佳佳走到门口,看到整栋筒子楼的居民,都自地围站在楼道里。
卖菜的、修车的、看门的老人们,每个人手里都攥着一把黄沙。
赵志忠老人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站在人群的最前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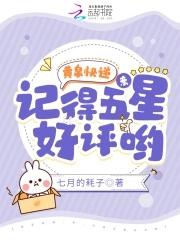

![我用魔法特产抚养幼崽[星际]+番外](/img/99436.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