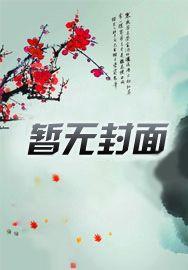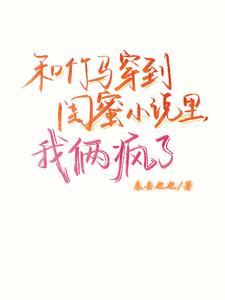富士小说>荒()离() > 极寒地狱(第2页)
极寒地狱(第2页)
而城外,则是另一番天地。
花溪北门外,那片临时难民营地,在寒潮来临前,已建起十馀座灰泥火炉,是林青禾主动请王旺带话,出人出料,为流民们烧制而成。
这些火炉多仿照竈体结构,以青壮带老人丶带孩子的家庭为单位分炉使用,日夜不断地烧。火炉旁的土地,被无数双冻脚踩得黑硬光亮,灰泥缝中嵌着手指印丶脚印,还有孩子的涂画。
炉子边,常常挤满人群,烘着手丶暖着脸。小孩子们不再整日缩在角落里发抖,也学会抱着竹片丶破碗去接炉火灰烬中烘热的芋头。
炉火燃起的,不止是温度,还有盼头。
可这盼头,并不足以抵御真正的极寒。
那年冬日最凛的一夜,北风呜咽,寒气宛如寒毒入骨,连烧红的火炉都不再滚烫。
次日清晨,总有几人再也没有醒来。
他们躺在旧衣草席中,不曾挣扎,像是沉沉睡去般,悄无声息地被寒意夺走了最後一口气。
再远一些,离开炉火丶没能轮到取暖的地带,甚至有人将死者层层叠放,草席裹尸,堆在一块角落里。
那尸山,已有近人高。
那是寒冬的代价,是所有人都知却又无力改变的沉默现实。
*
这一年冬天,仿佛连天地都闭了气息,整个世界都沉入冰封的深渊。
花溪城地处西南,向来冬短雪薄,从无真正的极寒年景。但今冬,却连这里的井水都三日不化,柴火劈开来中间竟结着冰霜,孩童走路沾湿鞋底不过半刻,便冻成硬块。
人们这才意识到,北地的寒冷,是何等吞噬生命的巨兽。
花溪都如此,更北之地,又该如何?
那是一片更早入冬丶也更难熬的苦地。
据流民口中断断续续传来消息,大寒之夜,整个村庄冻毙过半,“一个屋子八口人,只醒两个”的事,哪里都是。
有的人为取暖围着炭盆坐着,睡着了,再没醒过来;有的孩子裹在破被中,半夜被母亲抱在怀中,清晨却冷成冰石;还有人因无衣无食,夜里削屋木烧火,白日却再也没力气爬起。
而在这些死亡的背後——没有任何记载。
宣末帝,自北地大崩溃後便率文武百官南渡,立临安为新都,从此便深居简出,不问国政,不接奏章。
“冻死多少人”?
没有人能回答。
因为,他不问。
他不问,便可以假意不知千万百姓正在一个又一个的地狱中挣扎。
他不听,便可以继续沉醉在“南都行乐图”中,做着穷奢极欲的梦。
——“反正冻死的,不是他。”
终于,当极寒逼至极点,当死者尸体叠满山谷,无数人彻底失去等待与忍耐的希望。
在北方,在中原,在一些本就已被战争丶饥荒丶匪患反复蹂躏的土地上,反旗被悄悄扯起。
这不是有组织的军起,而是绝望的流民潮。
他们结成群丶围在一起,扛起木棍丶锄头丶破旗,穿着单衣,嘶吼着冲向封闭城门,冲向守军丶向衙署——
就像飞蛾扑火那般,明知无望,却仍要燃尽最後一丝怒火。
他们不想再死在雪中,她们宁愿死在抵抗中。
这一年冬天,人祸终于借着天灾的缝隙,浮出水面。
城池封闭,粮仓紧锁,兵丁守门,刀剑雪亮——
但这阻止不了,被逼到尽头的百姓,掀起更大的风暴。
那是一个旧王朝的深冬。
也是,另一场混乱与涅盘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