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小说>综武侠我当魔教劳模的那些年 > 第27章 牡丹 新马王爷有几只眼(第4页)
第27章 牡丹 新马王爷有几只眼(第4页)
更让他窝火的是,大狗也得看主人,这个刁毒的铃医,竟还打伤了他慕容家的弟子……
他这口气,怎麽咽得下?慕容明珠没处宣泄,就一股脑全泼向了尤明姜。
萧老板那边他得陪着笑脸,难道对你这个江湖铃医,还不能出口气?
骂不得萧老板,还骂不得你?
。
尤明姜斜睨他一眼,眼中尽是嘲讽:“①我懒得跟你说道理,你不配听。”
先前事发突然,没来得及细想这人来历,这会儿看清他的装扮,如今瞧他这一身行头,十有八九是那群紫衣人的头目。
早知道,她方才就该连他一起拾掇了,也省得听他在这儿狺狺狂吠,扰人清净。
慕容明珠一噎,脸涨成了猪肝色,半天想不出回嘴的话。
他心底的恨意翻涌,忽想起这人心狠手辣,可不是任人拿捏的翠浓,只能强压着,脚下重重碾了碾地面,以此泄愤。
。
这时候,翠浓已缩成一团,她像被猎狗盯上的小鹿,恨不得找条地缝儿钻进去才好。
感受到了她的不安,尤明姜搀扶起翠浓,擡手轻按上她的後脑勺,将她的脸埋进自己颈窝,低声安抚道:“别怕,我带你走。”
萧别离闻言,眼神玩味地看向尤明姜,询问道:“尤大夫,你刚才说……要带翠浓走?”
“不错。”尤明姜应得干脆。
萧别离挑了挑眉,扫了眼神色紧张的翠浓,又看看神色坦然的尤明姜,突然哑然失笑:“这可不行。”
尤明姜冷冷道:“不行?萧老板要是觉得不行,不妨试试拦我。”
萧别离轻叹道:“翠浓可是我无名居养着的牡丹,天生的娇贵,向来得人精心护着。离开了熟悉的水土,熬不住,会早早凋零的。”
亏他还敢提什麽养花!
要是这也算养花,那翠浓这朵花在他手里,简直被养得一塌糊涂!
眼睁睁看着禽兽们摧残一朵柔弱的花,任谁都没法真正保持冷静。
一股火气堵在胸中,硬生生憋得她心口发疼,尤明姜压下眼底厉色,隐忍道:
“萧老板这话可不对。凭栏圈养的那是供人赏玩的盆景,没了自在生长的尊严,再金贵的品种,也早失了魂儿。牡丹这花,历来是不冻不开的,越经霜雪,根扎得越稳,开得越盛,又怎麽会轻易凋零呢?”
“呵呵,只怕是尤大夫懂花,却不懂人。咱们说的都不算。跟不跟你走,可得问问翠浓的意思。”萧别离话锋一转,又看向翠浓,“我不阻拦你,你本就是自由身,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离开这儿……”
他顿了顿,意味深长地补充道:“不过,你可得好好想清楚了。”
听懂了他的弦外之音,翠浓垂着头,下意识抱紧了怀里的琵琶,不敢掉下泪来。
脑子里闪过马空群的叮嘱,她咬着嘴唇,内心挣扎不已,终究还是忍着心口的灼痛,摇了摇头。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快要听不见了,慢慢道:“尤大夫……我真的喜欢这儿。”
她是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女,那位从未认过她的父亲马空群,从不让她姓“马”,只让她留在无名居用妓女的身份作掩护,人前陪笑承欢,人後把江湖秘闻一一记牢,再递出情报。
这便是她这辈子被认定的唯一用处。
她活了十八年,没被马空群正眼看过一次,唯一的念想,就是哪一天能替他办成事,换一句“你没丢我马空群的脸”。
况且,如果她走了,母亲的坟墓和牌位,会不会被暴怒的父亲给毁掉?
。
这种腌臜地儿,怎麽可能真心喜欢?如果那是喜欢,翠浓眼里怎会有绝望的挣扎?
尤明姜只觉荒谬,半点儿不信。
还想再说什麽,翠浓却突然往後缩了缩。
“别管我了……”她别过脸,泪珠子砸在琵琶弦上,溅起一串儿细弱的响,“我这样的人,能有个地方待着,就已经很好了……”
她没说的是,如果连这儿都待不住,她连每年去坟前祭奠母亲的机会,都没了。
。
萧别离靠在轮椅背上,手指漫不经心地敲着扶手,“翠浓心意已决,尤大夫这一趟,怕是要无功而返了。”
令人意外的是,萧别离这声嘲笑,反而让尤明姜又定住了心神。
她明白了。
苦衷。
翠浓心里压着说不出的苦衷。
如果翠浓心底的苦没有真正化开,即便走出了无名居,那些无形的枷锁,终究仍会将她拽回这虎狼窝之中。
是自己太天真了。
救赎从不是一蹴而就的光,哪能指望一伸手就照亮所有暗处?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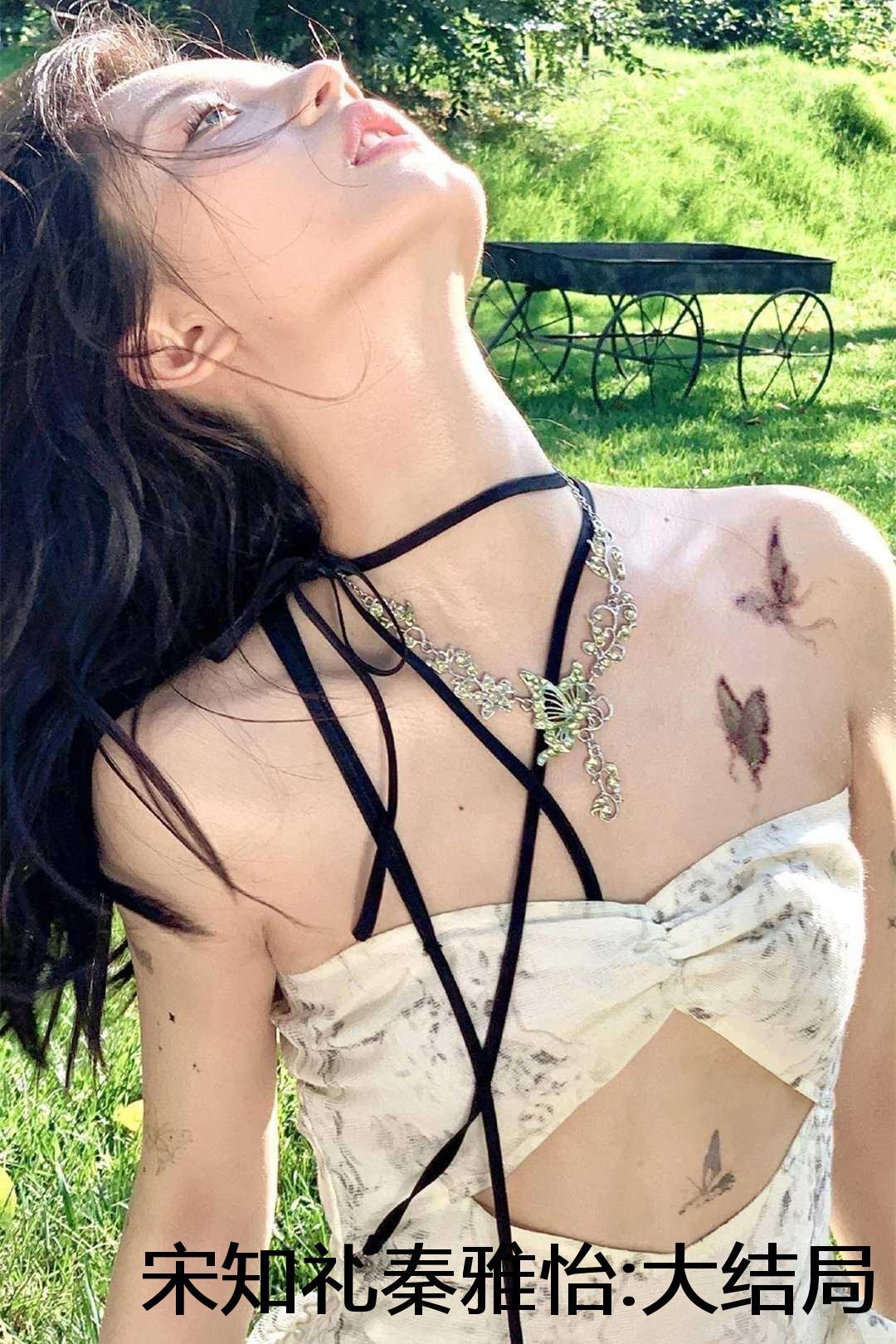
![盗版万人迷[快穿]](/img/4789.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