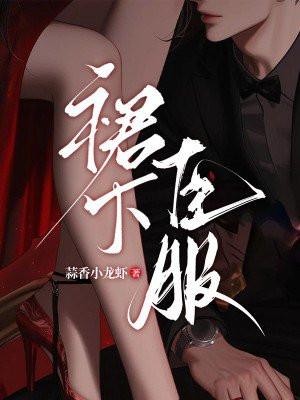富士小说>穿成太子的掌上娇 > 第154章 番外四 帝师受难记(第1页)
第154章 番外四 帝师受难记(第1页)
第154章番外四:帝师“受难”记
春末夏初,御书房内。
太子太傅周文渊须发皆白,手持戒尺,一脸严肃地站在书案前。年仅六岁的小太子苏庭,正襟危坐,小手握着毛笔,一笔一画地临摹字帖,小脸绷得紧紧的。
周太傅学问渊博,治学严谨,是帝师的不二人选。然而,这位老臣有个“缺点”——过于恪守古礼,对小太子的要求严苛到了近乎不近人情的地步。坐姿丶握笔丶甚至呼吸的节奏都有规矩,稍有不慎,戒尺虽不真打,但那严厉的训诫和失望的眼神,足以让年幼的太子战战兢兢。
苏宸偶尔过来抽查功课,见儿子小小年纪被管束得如同木头人,眉宇间难掩压抑,心中不免有些心疼。但他深知周太傅忠心耿耿,且严师出高徒,自己当年也是这麽过来的,不便过多干涉。
这日,苏宸与林砚一同来看太子功课。只见小苏庭因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手腕微微发抖,一滴墨汁不慎滴在了雪白的宣纸上,晕开一小团污渍。
周太傅眉头立刻拧紧,声音沉肃:“殿下!心浮气躁,何以治学?字如其人,一点污渍,便毁了一篇功夫!今日这篇《劝学》,重写十遍!”
小苏庭眼圈一红,却不敢哭出声,只得低下头,小声应道:“是,太傅。”
苏宸眉头微蹙,刚要开口,林砚却轻轻拉了他的衣袖,递给他一个安抚的眼神,然後缓步上前。
“太傅息怒。”林砚声音温和,他拿起那张被污损的字帖,仔细看了看,微笑道,“殿下年方六岁,能静坐临帖半个时辰,笔力已见框架,实属难得。这滴墨迹,依臣看,倒像一只误入纸间的小蝶,若能顺势添上几笔,或可化瑕疵为趣味,让殿下明白,有时‘错误’亦可生出‘意外之喜’,未必全需扼杀。”
周太傅一愣,看向林砚。他对这位天策上将军的才学能力是敬佩的,但对其偶尔“离经叛道”的思维却不敢茍同:“林大人,治学需严谨,岂可儿戏?”
林砚不慌不忙,取过一支细笔,蘸了少许淡墨,在那滴墨迹周围轻轻勾勒数笔,果然,一只栩栩如生丶振翅欲飞的墨蝶跃然纸上,原本的污渍成了蝴蝶的身体,浑然天成。他又在空白处题上一行小字:“学海无涯,思趣为舟。”
小苏庭看得眼睛都亮了,满是惊奇和崇拜地看着林砚。
林砚将笔递给小太子,鼓励道:“殿下试试?读书写字固然要认真,但若一味苦熬,失了趣味,便如鸟儿折翼,难以高飞。偶尔让思绪飞一会儿,无伤大雅。”
苏庭怯生生地看了周太傅一眼,又看向自己父皇。苏宸眼中带着笑意,点了点头。
小家夥这才鼓起勇气,学着林砚的样子,在另一张纸上小心翼翼地画起来,虽然稚嫩,却充满了兴致。
周太傅看着这一幕,眉头依旧皱着,但看着小太子脸上久违的光彩,终究没再斥责,只是长长叹了口气。
自那日後,林砚便时常“偶遇”太子下课,或带他去格物司看新奇的水力模型,或在校场用简易的弓弩教他射箭(当然是特制的丶毫无危险的小弓),甚至只是在御花园里,指着奇花异草讲解它们的习性丶用途。
林砚从不板着脸说教,而是将道理融入故事和实践中。他告诉苏庭,为君者,既要知书达理,也要通晓民生百工;既要守规矩,也要懂得变通;既要威严,也要有仁心。他讲朔方风雪中军民一心抗灾,讲清州浊浪里百姓如何守望相助,讲凉州城下将士们为何拼死守护家园。
小苏庭听得入了迷,在林砚面前,他不再是那个必须时刻紧绷的小太子,而是一个可以提问丶可以好奇丶甚至可以偶尔撒娇的孩子。他的性格肉眼可见地开朗了许多,眼神中也多了灵动和思考的光芒。
周太傅起初颇为忧虑,几次向苏宸进言,认为林砚此举会带歪太子,使其“不务正业”。苏宸却只是笑笑:“太傅,庭儿是储君,未来要治理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丶复杂的大雍,而非书本上的僵化教条。阿砚教他的,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人情’与‘世故’,是‘变通’与‘担当’。朕觉得,很好。”
一次,周太傅布置功课,让苏庭写一篇《论仁政》。小太子苦思冥想,写出的文章虽引经据典,却空洞无物。周太傅不甚满意。
恰逢林砚过来,看了文章後,没有点评文章本身,而是对苏庭说:“殿下,明日我带你去京郊的皇庄住两天可好?”
苏庭惊喜地看向父皇,苏宸点头允准。
林砚带着小太子去了皇庄,让他亲眼看看农人如何耕作,听听老农讲述年景收成丶赋税轻重丶官府吏治如何直接影响他们的生活。甚至让苏庭亲手尝试了扶犁(当然是象征性的)丶喂了鸡鸭。
回来後,苏庭重新写了一篇《论仁政》。这一次,他没有堆砌华丽辞藻,而是写下了自己看到的丶听到的丶感受到的。他写老农皲裂的手掌和看到好收成时的笑容,写村里孩童因为新设的义塾而能读书识字的喜悦,写对“仁政”最朴素的理解——让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幼者有所教,老者有所养。
文章交上去,周太傅看完,沉默了许久。文章谈不上文采斐然,却字字真切,充满了温度与力量。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教了半辈子圣贤书,或许真的忽略了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将心比心。
从此,周太傅对林砚的“插手”不再那麽排斥,甚至偶尔会主动询问林砚对某些课业的看法。御书房的氛围,不知不觉间缓和了许多。小太子苏庭,则在严师与“趣师”的共同引导下,健康地成长着。
苏宸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一次晚膳後,他牵着林砚的手在宫中散步,忍不住笑道:“朕看周太傅如今见了你,眼神都复杂得很,又是敬佩,又是无奈。你这‘帝师克星’的名头,怕是跑不掉了。”
林砚莞尔:“臣只是希望殿下能有一个更快乐的童年,将来能成为一个懂得百姓疾苦的明君。”
“有你在,朕很放心。”苏宸停下脚步,夜色中目光柔和,“你不仅是朕的良臣,亦是庭儿的良师。朕之幸,大雍之幸。”
月光如水,洒在两人身上,将身影拉长,交织在一起,如同他们共同为这个帝国未来所铺就的道路,坚实而充满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