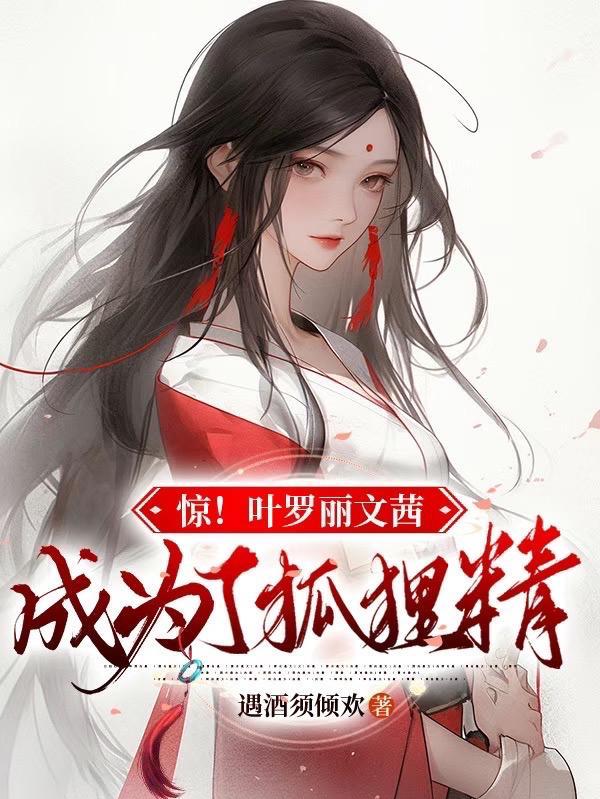富士小说>庶女攻略皇后 > 第374章 哑了的嘴最会听风声(第1页)
第374章 哑了的嘴最会听风声(第1页)
冬至后的第十日,天未亮透,京城的巷陌仍笼在一层薄霜里。
风停了,雪也歇了,可寒意却比前几日更沉,压得人喘不过气。
但这一夜,城南、城北、城西的街坊小院里,灯火竟迟迟未熄。
不是官府许的灯,也不是书院开讲的夜读——是百姓自围坐在炉边,一人一段话,一句一段事。
没有铜哨,没有竹简,甚至连纸都不用。
他们只用嘴说,用心记,把那些曾登过《民声志》的冤情灾案,一桩桩讲出来。
有个老农坐在自家灶台旁,手捧粗碗热汤,声音低哑:“三年前那场大水,堤坝早裂了口子,可县令不许报雨情,说‘妄言天灾者斩’。我儿跑去省城递状子,半路被截回来,打残了一条腿……后来汛期一到,整个村子都淹了。”
旁边一个妇人抹着眼角:“这不就是我娘家的事?那年《民声志》登过一篇《七村淹册》,写的就是沿江七村没人管……我当时还不信,以为是瞎编的,现在才明白,人家早替我们喊过冤了。”
茶肆角落,盲眼说书人拄着竹杖,嗓音沙哑如磨石:“今夜不说传奇,不说忠良将,就说一件真事——幽州工役案。三百民夫修渠,冻死十九人,监工却报‘病故’。有个小子临死前写了封信,藏在鞋底,靠一只铜哨传到了城里……信上只有四个字:‘我们冷’。”
底下有人抽泣,有人攥紧拳头。
没有人组织,没有人号召,可每一场“口述夜”结束时,总会有个孩子怯生生地问:“娘,这些还能不能登报?”
大人沉默片刻,摇头:“现在不能了。”
孩子又问:“那以后呢?”
没人回答。但那一双双眼睛里,已不再只是恐惧。
消息传到七王府时,崔明瑜正在整理旧档。
她听完探报,指尖顿住,抬眼望向窗外檐下挂着的那只铜哨——它静静悬着,纹丝不动,仿佛连风都不敢惊扰。
她轻声道:“他们不再等我们声了。”
苏锦黎站在廊下,一身素色深衣,未全挽,只用一根木簪别住。
她望着那枚铜哨,听见的是千家万户的低语,是无数个夜晚未曾熄灭的灯火。
她忽然笑了,很轻,像风吹过枯叶。
“这才算真正活过来的声音。”
她转身回房,取来一张桑皮纸,铺在案上。
纸上无字,但她仿佛看见了万千笔迹正从民间浮起,汇成一条无声奔涌的河。
与此同时,赵砚舟换了身布衣,混入城南一家不起眼的茶肆。
他是奉内阁密令而来,查“口述夜”是否为王府煽动之举。
若属实,便可定性为聚众惑民,一举铲除余患。
他坐进最偏的角落,点了一壶粗茶。
台上盲人正讲到《灾音录》中一则旧案——某县令隐瞒旱情,强征秋粮,致饥民易子而食。
台下一名妇人忽然失声痛哭:“这是我娘!她临死前就这么喊的!你们怎么都知道?”
赵砚舟心头一震。
他本想记下几句“煽动言论”好交差,可听着听着,竟提不起笔。
这些人没有旗帜,没有名录,甚至不知彼此姓名。
他们只是记得,只是愿意说出来。
次日清晨,他独自上奏,仅寥寥数语:“民声如野火,不在册中,在心里。”末尾附议一条——建议将“口述传承”纳入乡学考评,以助记忆延续。
奏折递上去那一刻,他自己都怔了片刻。
他知道,这不是任务的完成,而是立场的转移。
而在城东几处学塾外,沈琅派出的眼线早已盯了三天。
宫中便衣吏员每日巡查,手持小册,记录孩童吹奏的哨曲是否“合规”。
起初还警惕异常音律,后来现全是节气歌谣,什么“春分燕来鸣”“谷雨雷初响”,便松了口气,上报“无异常”。
但他们没听出,这些看似寻常的旋律,每个起音都暗合《缄言录》中受害者的姓名音——李、王、陈、吴……七十二个名字,藏在二十四节气的曲调里,循环往复,如影随形。
当最后一段“冬至阳生”响起时,王府地窖深处,三十六口磁瓮同时共振,将分散的音律还原成完整的密码陈情。
萧澈听完暗卫汇报,倚在暖阁窗前,唇角微扬。
“他们查调子,我们藏名字。”
他说得平静,眼里却有锋芒闪过。
这几日,朝堂表面平静,实则暗流汹涌。
皇帝虽允《民声志》续办,却加了“御览备案”之限,分明是试探与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