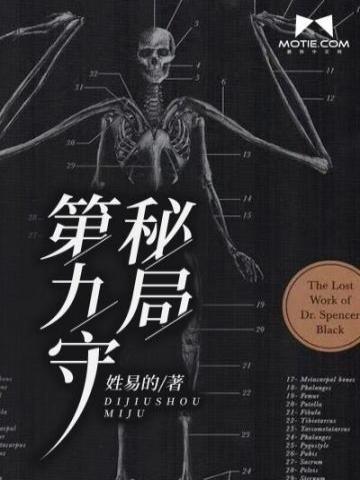富士小说>花魁的拼音 > 嫁衣(第2页)
嫁衣(第2页)
萧世祯在泽州黄袍加身,成为天下新主,改国号为“燕”,改年号为“太平”,定国都于幽州。
他留下郝景处理地方军务,御驾回京。
自从在青州分离,我们之间频繁书信往来,但自始至终他没有提起萧阮,我也没有。
我猜谢妈妈已经把那天的事告诉他,但他不想让我感觉是在派人监视我,因此不提。
登基称帝的事,他也只是在信里潦草一提,仿佛谈论吃到了某道新出品的菜肴。
倒是长篇累牍啰啰嗦嗦地与我商议,帝後大婚的婚仪要如何操办。
我没有回应他婚仪的事,只嘱他路上留意散兵游勇,千万保重。
我知道他本是闲云野鹤的性子,对权力没有那麽热切。
但现在三军上下为他打造的这件黄袍,他必须要穿。
且不说天下是以他的名义打下来的,军队和银饷多是他出的,就算他有心想让贤,而被让贤的人真敢接手皇位,他也不能让。如果他让了,日後必反遭清算——谁放心这麽一个有钱又有名望的人浪迹江湖?万一哪天他又想找个皇位坐坐怎麽办?
所以皇位只能自己坐。
这道理不是萧世祯说的,是我说的,我写在信里的。
他回信说:“知我者猗猗。”
燕侯成了皇帝,燕侯府的规格按礼制也要拓建成皇宫。
我嫌施工太吵,想和虎儿搬出去,萧世祯不许,反倒把拓建工程叫停了。
他是生怕我走。
于是我便在府里等他回来。
临近回府那天,太常寺官员欲安排我们如何如何迎驾,却因我的身份而犯了难。
萧世祯後院空空荡荡。外界知他曾有过一位夫人,但明面上已经死于幽州城外张各村。身边唯一的一个我,身份秘不示人,没有任何品级,却带着他的孩子。
若当我是妻,我与他并无婚礼。若把我当成妾来安排,太常寺又怕得罪了我。
我看出这些官员的局促,轻松一笑:“那日我称病不出就是了。”他们这才松了口气。
于是他回来时,在门外受了衆人的礼,直奔後院来见我,我只随意向他福了福,仍是我们私下见面的礼节。
他试探着走近我,试探着抱了我,抱住了就不松开。
“你没逃跑,真好。”
我笑道:“你做了什麽对不起我的亏心事,生怕我跑?”
感觉他抱我抱得更紧了。
我心中暗叹。
听见他说:“若换成是从前的你,是不是早已跑走了?”
我在他衣袍的沉水香气中莞尔:“是。”
“你决定相信我了吗?”
“是。”
“不怕我骗你。”
“是。”
“我做了皇帝,如果将来我欺负你,你是会很惨很惨的。”
“我知道。”
“猗猗,猗猗……”他双臂紧紧搂着我,愉悦地叹息。
他说他一路都在犯愁该如何向我解释当年的事,中间一度觉得皇位碍事,险些要让贤,接了我的信才打消了念头。
毕竟他一旦做了皇帝,找再多证人来向我论证他没有和白妈妈联手拿合欢蛊唬我,我都不会完全相信,而会始终怀疑证人是否屈从于皇权而说谎骗我。
萧阮临终前留下的那些话,句句诛心,楔在我和他信任最薄弱的地方:我们的定情之始。
如果爱的发生是建立在世祯对我的算计之上,以我的多疑和缺乏安全感,爱的堡垒无论盖得多高,都会瞬间坍塌。
萧阮很了解我,但他不知道的事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