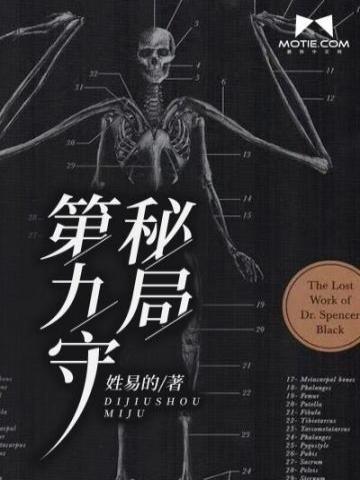富士小说>螳螂猎宴byw笔趣阁TXT > Chapter 66(第3页)
Chapter 66(第3页)
只听一声粘腻而清晰的“咔嚓”声,螳螂酷寒的骨镰猛然透穿了他的脖颈,纤薄锋锐的尖端嵌进了最细腻的骨缝里,再猛一发力,就将那截脆弱的嵴骨当场撬断,一簇鲜血伴随着雄虫撕心裂肺的哭叫声喷射而出!
他的後颈如蝶翼般敞开,鲜红黏腻的血肉还在层叠着蠕动…里头卧着两截断裂的丶森白而狞恶的颈椎骨,上半截被螳螂的骨镰牢牢钉进了他身下的天鹅绒坐垫里,下半截则从雄虫颈後狰狞地破土而出,活像一截病态而肥腻的蛇首。
从没有雄虫能忍受如此恐怖的痛感,时绮浑身抽搐着不住打颤,还在惊恐且震怒地挣扎,甚至不忘扯着嗓子尖叫“你们怎麽敢”丶“我可是高阶雄子”之类的字眼…下一秒就被几根遒劲的手指猛地刺进了脖颈深处,就像一柄利刃挤进了肥嫩软腻的蚌肉,活剥出一串莹润饱满的珍珠——
他被雪栀徒手扯断了声带。
“你太吵了,都让我听不清楚妈咪在说什麽了,”雪栀叹息道,“就没人教过你礼貌麽?”
那截软腻的声韧带还裹着湿淋淋的血丝,就像虾线一样被扯了出来。
连声音都发不出来,时绮瞪圆了眼睛,仅能从破碎的喉管里发出“呵呵”的鸣喘声,喉头的脓血如喷泉般喷射得满地都是,又被螳螂美人笑盈盈地擒着那不断垂死挣动的四肢,隔着雄虫漂亮齐整的西装,以极为细腻温柔的按摩手法——
将後者的骨骼一截一截地折断,再一寸一寸地揉碎成了烂泥。
恐怖的痛觉在这具柔弱的身躯里持续不断地爆发,雄虫浑身冷汗淋漓,几乎痛死过去。
被螳螂美人用柔润温热的掌心抚摸着那截突出的颈柱时…他只能半哭半哑地细声哭噎,于是瑭的抚摸逐渐透出极为缠绵的柔情与蜜意,就像在抚摸幼兔可爱又敏感的小短尾巴,或者…一柄骨头雕就的丶象征滔天权势与无上荣华的手杖。
就在这时,瑭手掌猛地捏住了雄虫裸露的下半截颈椎,将其後衔接的整截嵴骨连根拔起!
“……!”
在雄虫模糊不清的惨叫声中,那片苍白的丶被保养得肌肉紧实丶皮肤细腻的嵴背上鲜血横流,从猩红外翻的皮肉里拱起一截截森白的嵴骨,状若狰狞的蜈蚣,一路从後颈血淋淋地裂至尾椎。
雪栀修长的…不染纤尘的漂亮手指,便精准地落在了雄虫嵴骨最中间的那一环。
最肥美的骨髓被黏膜和神经纤维包裹,就藏在牡蛎般坚硬的骨骼里,此时被雪栀利落而优雅地撬开,两指往骨腔里从容地一勾,便将那团肥腻软烂的髓浆剜了出来。
然後…他微微皱起眉,将那团骨髓缓慢地吃进了自己嘴里。
车厢里遍地狼藉,满地都是猩红的淤泥,甚至找不到坐的地方。
一件温暖而奢华的白狐裘皮大衣被垫在了瑭的身下,细绒毛领掩过美人皓白秀美的天鹅颈,活像一团暖融融的白雾,暧昧地摩挲着美人如贵妇般温婉明丽的脸庞。
雪栀替母亲仔细地扣好纽扣,後者穿着单薄的睡裙,跟着他在雨夜里乱跑了不知多久…一身莹白丰腴的皮肉早已湿透,简直跟全裸没有两样,瑭却一副满不在乎的模样,还拿着不知从哪里掏出来的丝绸手帕,擡着手仔仔细细地擦拭宝宝唇畔残留的血污。
这位熟透的母亲…连衣服都顾不得换,就光顾着惦记他心爱的宝宝了。
雪栀用馀光瞥了一眼沙发上的那滩烂肉,居然还在微弱地喘气:
“那家夥怎麽处理?”
“唔…”瑭也苦恼地皱起鼻子来,思索了几秒,又笑逐颜开道,“把他拖到车子後面吧!”
在他那张漂亮到堪称杀器的脸庞上,笑意明媚又张扬,天真又残酷,简直能叫黑暗心生怯意。
他笑着说:
“我要向全世界展览我刚捕到的猎物!”
浓稠的雨幕里,这辆尊贵的礼宾车停泊许久,终于重新啓动,车尾坠着一坨不起眼的丶还在挣扎蠕动着的肉团,时不时还会发出一声凄厉又模糊的尖叫,在粗粝的道路上拖出一道长长的血痕…很快就被暴雨冲刷干净。
车厢里,一切渐渐归于静谧,不时传来爱人厮磨时轻轻的笑声和黏腻的舔吻声。
那些效忠于时绮的虫卫们都安静而肃穆地待在原本的岗位上,在信息素的无声操控下,连雄主的惨死都毫无察觉,车厢里是死一般的寂静…不知过了多久,只能看到一只素白的丶柔软的手掌,从沙发椅下小心翼翼地探出来。
那是“猫”。
整个杀雄的全程,他都害怕地躲在座椅底下,此时终于敢偷偷伸出一只手来,好奇地拨弄了一下那枚滚落在地毯上的嵴椎骨。
就像小猫玩球一样。
诸君,比起真刀实枪,我好像更喜欢写各种瑟瑟的擦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