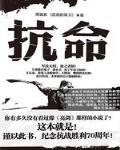富士小说>浮世双娇传金盏剧照 > 第188章 衣钵相承寄厚望(第2页)
第188章 衣钵相承寄厚望(第2页)
他转向父亲:“父亲,请您主持大局,孩儿有一计”
三日后,沈家老宅来了一位不之客。
来人自称是金陵商会的会长,想要与沈家洽谈合作。但明辉一眼就看出,此人步履沉稳,眼神锐利,绝非普通商人。
果然,寒暄过后,来人压低声音道:“明辉少爷,敝上赵大人托我传话:若肯交出宝物,既往不咎,还可保沈家富贵荣华。”
明辉不动声色:“若我不答应呢?”
来人冷笑:“那就休怪赵大人不讲情面了。沈家虽有些根基,但与赵大人为敌,无异于以卵击石。”
明辉端起茶盏,轻轻拨动茶沫,忽然问:“阁下练的是少林金刚掌吧?听说这套掌法刚猛无俦,但有个致命弱点——气走手少阳三焦经时,若遇反击,必伤肺脉。”
来人脸色顿变:“你你怎么知道?”
明辉微笑:“医武同源。阁下近日是否常感胸闷气短,夜半咳醒?”
来人惊疑不定:“正是”
“那是功法反噬之兆。”明辉取出一枚银针,“若信得过,我可为你诊治。”
来人犹豫片刻,终于伸手。明辉运针如飞,不过片刻,来人便觉胸中郁结顿消,呼吸顺畅许多。
“多谢少爷!”来人起身行礼,神色复杂,“少爷仁心仁术,在下佩服。只是赵大人那里”
明辉淡然道:“回去告诉赵守仁,宝物确实在我手中,但唯有德者方能得之。他若强取,必遭天谴。”
来人迟疑道:“少爷不怕赵大人用强?”
明辉目光坚定:“沈家世代行医,救人无数,这江南百姓,便是沈家最大的依仗。赵守仁若敢用强,先要问问百姓答不答应。”
来人肃然起敬,深深一揖:“少爷高义,在下一定把话带到。”
待来人离去,沈墨林从屏风后走出,欣慰地看着儿子:“处置得当,刚柔并济,已有家主风范。”
明辉却无喜色:“父亲,这只是缓兵之计。赵守仁不会轻易放弃,我们必须早做准备。”
接下来的日子里,明辉展现出了惊人的领导才能。他一面整顿家业,将杏林堂的业务拓展到江南各州府;一面暗中联络忠义之士,组建护卫力量。
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开始研读帛书上的治国方略,并走访民间,了解百姓疾苦。
这日,明辉与素心一同前往城郊的难民营。去年水灾后,许多灾民流离失所,明辉定期前来义诊。
“哥哥,你最近变了许多。”素心看着认真诊病的明辉,轻声说。
明辉为一位老妇诊完脉,开了药方,才回道:“哦?哪里变了?”
“变得更加沉稳了。”素心思索着用词,“像是忽然间长大了十岁。”
明辉苦笑:“或许是明白了肩上的责任吧。”
他望向远处衣衫褴褛的灾民,目光深邃:“从前只知道行医救人,现在才明白,治一人之病易,治天下之病难。这帛书上记载的治国之道,字字珠玑,但若不能真正理解民间疾苦,终究是纸上谈兵。”
一位老者颤巍巍地走上前来:“沈大夫,多谢您这些日子的照顾。小老儿无以为报,只有这个”他掏出一块粗布包裹的物件。
明辉打开一看,竟是一本手抄的《流民安置策》。
“这是”明辉惊讶地看着老者。
老者道:“小老儿原是县衙师爷,亲历三次大灾,深感现行赈灾之策多有不足。这些年闲来无事,便将一些想法记录下来,或许对沈大夫有所帮助。”
明辉细细翻阅,越看越惊。这本手抄本虽文笔质朴,但所提建议切实可行,许多想法与帛书上的治国方略不谋而合。
“老先生大才!”明辉由衷敬佩,“不知老先生可愿助我一臂之力?”
老者惶恐道:“沈大夫言重了。若这些粗浅之见能帮到百姓,小老儿荣幸之至。”
回府的路上,明辉一直沉默不语。素心忍不住问:“哥哥在想什么?”
明辉道:“我在想,民间有多少这样的贤才,因无门路而埋没。若能广纳贤士,集思广益,何愁天下不治?”
素心笑道:“哥哥越来越有伯父的风范了。”
明辉却摇头:“我还差得远。伯父常说要明辨是非,如今我才明白这四字的分量。治国安邦,不仅要有一颗仁心,更要有明辨是非的智慧。”
转眼到了沈墨山的百日祭。这一日,沈家老宅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客人——有受过沈墨山恩惠的百姓,有他生前救治过的病患,还有不少闻讯赶来的江湖义士。
祭礼结束后,沈墨林将明辉叫到书房,神色庄重。
“辉儿,今日当着诸位亲友的面,为父要正式将沈家托付于你。”
明辉怔住了:“父亲,您”
沈墨林摆手:“为父年事已高,又重伤未愈,理应将家主之位传于你。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些日子的观察,为父相信你能胜任这个重任。”
小主,这个章节后面还有哦,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