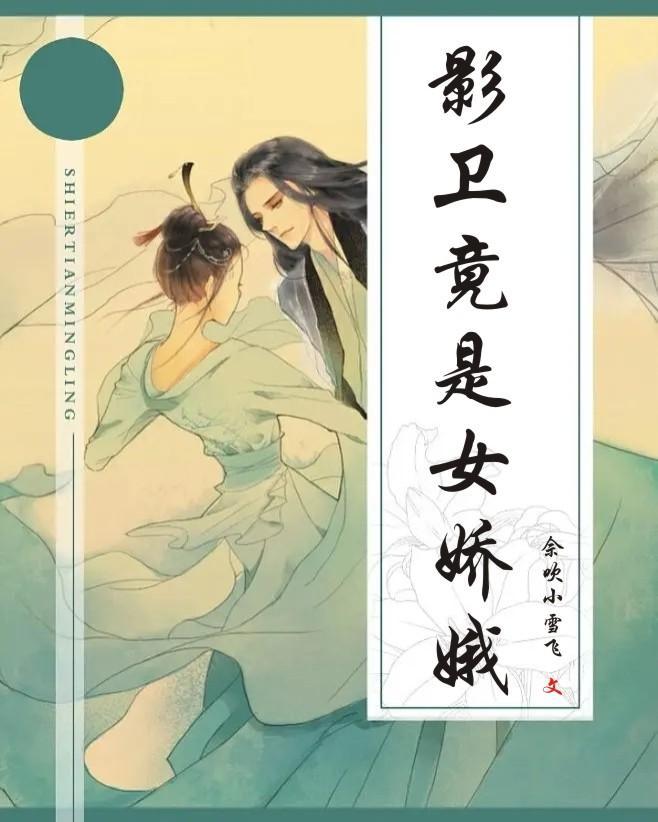富士小说>得体句子 > 七年前(第1页)
七年前(第1页)
七年前
彻底说开的这一天,路晔然还有一下午加一晚上的课,他和舍友的关系不错,上午的台词帮忙请了假。
浑浑噩噩地回到宿舍後,播音生刚爬起来,戴着耳机打游戏,见路晔然回来後问:“这两天怎麽了?”
他把烟盒扔给来人,路晔然摆手:“不了,我戒烟了。”
“这麽突然。”播音生奇怪地瞥了他一眼,继续专注打游戏,“你下午上不上课,不上课陪我打游戏。”
“我不玩游戏。”
“我教你啊,我反正是不想上课,最烦那老头,水课有什麽好上的。你上不上课?”
“外国戏剧…”路晔然念叨,“去上课,你自己玩吧。”
“晔然,你失恋了啊,怎麽一直怪怪的?”
他否认:“不算失恋,就是…就是,我不知道。”
“失恋就失恋,又没笑话你。”舍友开玩笑道,“别难受了,以後还会碰到更好的人,你歇会吧,吃饭没,我一会去买饭。”
“不吃了,你自己去吧。”
路晔然躺在上床,舍友还在下面念叨,他蜷缩着身体,大脑中竟然一直重复着我不知道这四个字,还不忘分出一丝精力在心中反驳,不会再遇到更好的人了,不会再有人比陈唯一更好了。
三年前高一暑假,学校里给每个人发了一张电影票,据说是某个知名企业家因为自己儿子获奖,包了数不清的场次,免费放到各地区学校里给学生看,路晔然对电影的了解仅限于电视上的电影频道。
他对电影不感兴趣,只觉得浪费时间,想把这张票卖出去,奈何演员导演实在不出名,题材也不符合大衆潮流。路晔然在商场四楼的电影院门口站了好一会都没卖出去,除了几个学校的学生,大部分来人的目标都是同期上映的喜剧片。
开场前五分钟,两个认识的同学来到电影院门口,他们发现三个人的票座位是挨在一起的,路晔然和同学都不怎麽熟,只有这两位还算好一些。
同学邀请他一起。
“我不看电影。”他说,“我想把这张票卖掉。”
其中一位同学很自然地接过他手里的票∶“你卖给我吧,我们一起去看,要到时间了,一会白费了。”
无功不受禄,路晔然很忐忑地看了同学一眼,两个人脸上都很平常,笑嘻嘻的,都是很好的人。
剧情还没开始,三个人快步走过去,刚推开门,映入路晔然眼帘的是大荧幕上的人,青涩的脸庞上浮着张扬的笑,他穿着西装,高举着金色的奖杯,嘴里吐出流利的英文,底下的中文翻译是:我不会止步于此。
每一根发丝都那麽完美,每一个五官都恰到好处,很明显地能看出年纪不大,高中生的样子,还没长开,他没有化妆,却很让人着迷。
路晔然推门的动作愣住,碰巧屏幕上的人扫视了整个观衆席,他竟然生出一种在看自己的错觉。
几秒钟的时间,却感觉过了很久,同学催促:“进去啊…怎麽回事,上火了吗?你快去趟洗手间吧,别弄衣服上。”
等坐到座位上影片已经开始,里面登场的主角年纪更小,都不是高中生,像初中生,路晔然眼睛不眨地看着整部电影,身边的同学已经睡着,这不是个很好玩的片子。
陈唯一宛如一尊闪闪发光的雕塑砸进他的世界,砸出个巨大无比的坑,留下不可覆盖的印记,雕塑是金子塑成的,不是金子,要比金子更贵,而且不需要保值。路晔然牢牢记住了演员表上第一位的名字,很适合他,是和他本人一样,完全独一无二,世界上仅此一件的宝物。
回忆被其他舍友的推门声打断,大家都很有边界感,没有问路晔然为什麽选择回来住。
偶然间聊天内容突然拐到关于祈福的话题,其中一个舍友的妹妹今年高考,寒假的时候去求了手链,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真的有用,说是发挥超长了不少。
路晔然爬起来,吓了舍友一跳。
“你干什麽去?”
“有事,我尽量晚上表演课之前回来。”路晔然头也不回,“剧组有事,我给导员请假就可以,谢谢大家了,回头请大家吃饭。”
他直奔祈福小庙,想知道陈唯一不想让他看到的内容究竟写了什麽,和五月一样,同样的老先生躺在门口的躺椅上,拿着羽毛扇子装神弄鬼地扇风。
路晔然翻找了好久,最後在桌子上看到了写过的册子,他问老先生:“师父,有人来找过这一本吗?”
老师父神秘兮兮,让他凑过来,在他耳边悄悄说:“你猜。”
路晔然没心情开玩笑,勉强笑了一下,翻看起来,翻来覆去也只看到了同样有两人笔迹的一页。
下一页就变成了其他人的笔触,路晔然摸着书缝,是有人撕下来了。
他苦笑出来,就这麽不想扯上一点关系,那为什麽还要留着前面一页。
路晔然看了眼时间,应该可以在晚上表演课之前赶回去,他今天一口饭都还没有吃,头晕眼花,道过别後就要往山下跑,老师父喊住他:“在山里晕倒可没人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