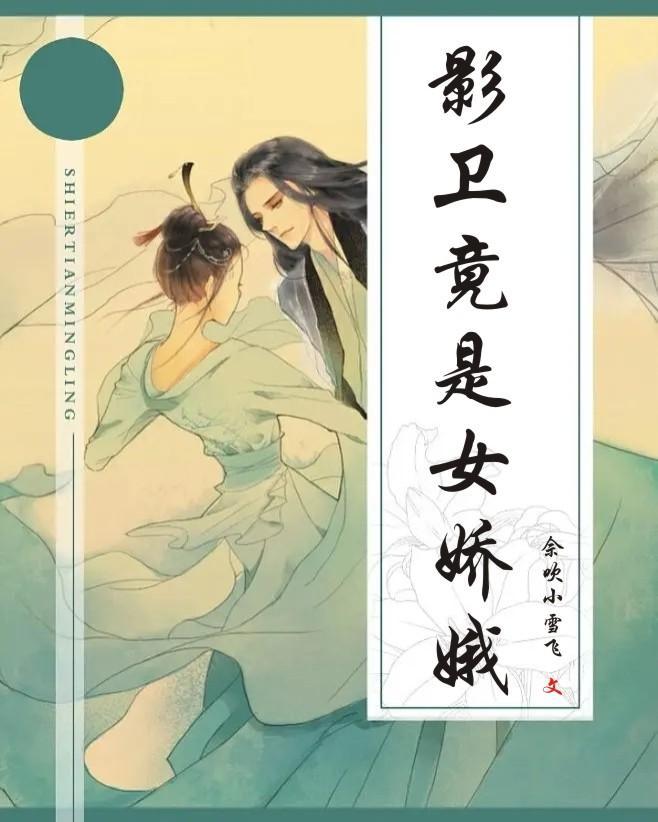富士小说>夫君他心有白月光 潘多拉密码 > 误会(第1页)
误会(第1页)
误会
两人之间差了一个头,郎俊女俏并立在梅树下,本是极其清新明媚的景色。
燕稷动作更是亲密无比,呼吸之间旖旎无限,谢灵犀闻言应激,一掌拍掉了他作乱的手,被抚过的脸皮涨得通红。
比梅花还要艳上三分。
背上伤口分明已然痊愈了,此刻又隐隐作痛,谢灵犀下意识扶了身旁一株树,雪中沁出的凉意冷不丁钻进她皮肤里,循着血液沾染五脏六腑。
她胡乱喘着气,试图缓和脸上热温,“……你慎言。”
见她连殿下都不叫了,燕稷生出一丝窃喜,自然展颜,温温柔柔道:“我还是更喜欢灵犀唤我陛下的模样。”
这些日子他在幻梦中沉浮,终于想明白了另一件事——
功成名就之外,自然得有红颜知己,贤良的皇後,思来想去,还是谢灵犀更合他的心意。
果真前世娶她为妻,是极有远见的。
前几日马车之上他试探谢灵犀,心中还尚存一丝愤恨,既痛恨谢灵犀如此心狠害他,又痛恨自己英明一世竟着了女人的道。
可如今他已恍然大悟,正是这般冰雪聪慧的娘子才配得上他呀!
他折了谢灵犀的羽翼,杀了她的亲人依仗,还怕重蹈覆辙麽?
于是又耐着性子重叙那日的话题,表明心迹:“只要你愿意来到我身边,前世之事既往不咎,待我登上皇位,你自然是名正言顺的皇後殿下。”
谢灵犀哪里料到他还是这般穷追不舍,心中烦躁,又想吐血了,恹恹道:“什麽皇後,我不愿做。”
抄她谢家,翻了她的箱子,收监了她的父兄,她还未找燕稷算账,这人反而深情款款地凑到她面前胡言乱语。
燕稷愈来愈疯了,身旁竟无一人提醒他麽?
“除非——”
谢灵犀忽然软和了身段,擡眸看向燕稷,端是一派秋水传神丶可怜可爱,“殿下若放了我父兄,还我谢家百年清名,我便答应殿下。”
燕稷自然不会答应。
他却也不恼,解释道:“这事儿并非师出无名,谢大人犯了错自要受到惩罚,我怎可徇私枉法。”
说的和真的一样。
谢灵犀问他:“既都是异世之魂,我自然将一切都打点好了,消了隐患,殿下如何还能从我府中查出我父兄贪墨?如今说他们犯了错,错在何处?”
此话一出,燕稷怜悯地看着她,眼前的娘子倚在梅枝一副弱柳扶风的模样,似乎风一吹便可掀到,大雪重了便将人压得动弹不得。
他叹息:“灵犀啊灵犀,你还是这般天真,能屹立百年的世家,谁家中没有点见不得人的污垢?”
他忽然钳住谢灵犀的双腕,死死盯着她的眼睛,“你真以为,你们家就这麽干净吗?”
“……”
谢灵犀不说话了。
周遭倏地静下来,只留飞雪满天。
见她霎时间被打击到,有如鲜妍的荷花一夜之间枯死,任人随意摆布了。
燕稷佯作不经意瞥了眼前来的模糊身影,双臂环上谢灵犀的腰肢,轻柔地将她的头按在怀中,哄道:“没事,没事了。”
那身影踏雪而来,迈着大步,寻觅四周,终于瞧见梅树下依偎着的两个人——
高的是震惊朝野的晋王,他将怀中姑娘抱得极紧,只露出来一角浅浅的衣裳……
柳续看清了那姑娘露出的衣角,分明是他亲自为他娘子描的花样,心惶惶的,手中的伞连带暖炉“啪”的一声砸在雪地中。
这时,燕稷乍然擡头,对上他的目光,透出势在必得之意。
柳续扯了扯嘴角,只觉天太冷了,嘴唇干得裂开,钻心的痛,连一丝笑也扯不出。
他闭了闭眼,淋着风雪,踉跄离去。
谢灵犀听到声响,推开燕稷,“什麽声音?”
燕稷唇角勾起,侧身挡住雪地中的一把伞与铜制雕花的炉子,手轻轻压放在谢灵犀肩上,“没什麽。”
……
柳续这些时日总躲着她。
年关将近,今晨她拎着篮子早早出门采了些冬寒菜,欲煮汤喝,刚踏进家中大门,便见柳续立在门边,跟一尊门神似的,脸也不笑,盯着她一言不发。
她挽过柳续的手,刚要同他讲话,便被这人倏地拔出小臂,板着脸走远了。
谢灵犀:“……”
若非清楚柳续的品行,她倒要怀疑当初柳续娶她存的是一些攀附之心了——如今谢家失势,便装也不装,对她爱搭不理。
到底出了何事?
谢灵犀百思不得其解,便回夥房揭开锅,悠悠洗净菜炖汤,甫一煮好,衆人围坐在庭院中石桌上吃饭。
见春桃丶初柳皆裁了新衣裳,柳枝也拿着月钱买了双新靴子。
谢灵犀想起前些日子她夜里悄悄为柳续绣的香囊,如今完工,正要拿来,忽然听柳续说:“怎麽不做新衣裳?”
语气冰冷,仿佛夹杂了河中三寸寒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