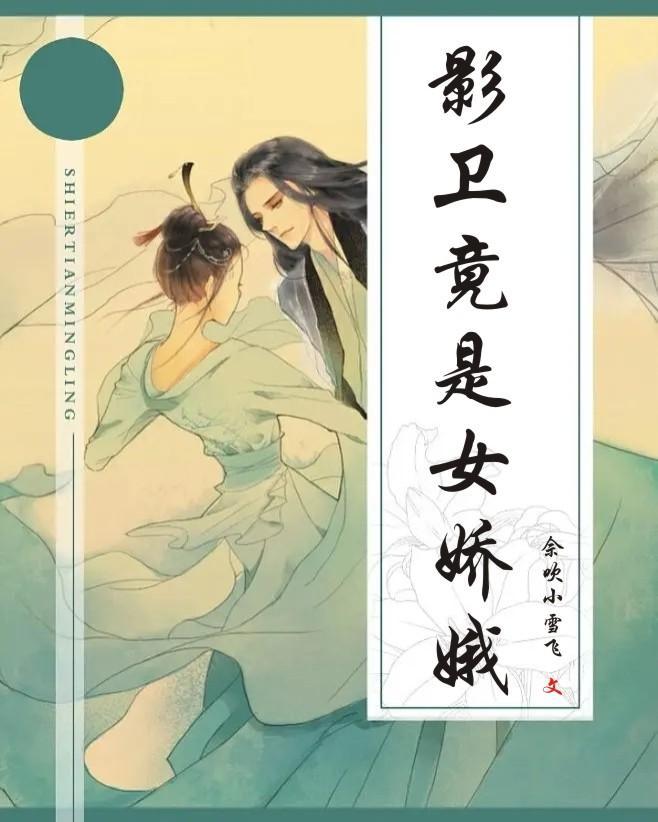富士小说>瞻云酒店 > 第31章(第2页)
第31章(第2页)
以上两种情况任其一,他都无法再同意温颐的提议。
而温颐,在这中间有扮演着什麽角色呢?
他在来向煦台前,就已经得到堂兄传来的尚书台讯息。曾几何时,他想让温颐接手的,今日看来,实不知该庆幸还是遗憾!
他疲惫又孤寂。
然而这一刻,他目光越过欺在他身上的男子,落在眉目锐利的女郎身上,上林苑生出的那点同袍之谊愈厚,石桥那一箭救他性命的感激更深,他恍惚有一瞬觉得,若有一日他倒下了,她也可以独自撑起他们未竟的使命。
——她竟然能有如敏锐的见解,竟然同自己想的如出一辙。
秋阳灿而不炫,日光披她身,薛壑觉得看见了江瞻云。
“未央宫中的那位主子可能如何?”薛壑恢复了神思,擡眸笑问申屠泓。
申屠泓被还在想薛九娘的话,被近在咫尺的声音拉回神,似是太多的事让他无法消化,一时间望向被他臂膀压地的人,黑白分明的眸光中竟有些不知所措。
“让开——”江瞻云提裙上来,牟足劲一把推开申屠泓,“一个个就会欺负我阿兄,有本事你到尚书府也这般问去。”
江瞻云扶起薛壑,瞥过申屠泓,口中尚未停下,“未央宫里的主子是谁?不就是天子吗,你想编排他甚?他可能是甚?是坏人?那我阿兄若是坏人,这会就该把你绑了面圣去。编排天子,乃抄家灭族的大罪!”
“让开!”她将薛壑扶进屋,见人挡在门口,又瞪一眼。
申屠泓却丝毫不恼女郎,虽然她的话闻来张狂护短,但对他简直醍醐灌顶。
若薛壑当真与明烨同流,于私这会尚在他府宅中,他可以直接了结自己;于公自己以下犯上,他可以名正言顺收押自己,然後再下手。
可是他什麽也没做,只将目光重新投过来,“下去吧,以前如何做,以後依旧如此。”
申屠泓见人微微涨起的嘴角,想上前又迈不开腿。
“作甚,要我唤人把你赶出去吗?”薛九娘怒气汹汹,“有这闲工夫,你且去尚书府问问!”
申屠泓僵了半晌,垂头拱了拱手,转身离开这处。
……
“大人怎麽不躲的?”桑桑去膳房取来冰块裹在巾怕中给他消肿,见原本就过分苍白的面容如今又红肿起来,嘴角还渗着血,心下不忍。
“再打两拳,阿兄都不会躲的。”江瞻云面无表情地拈着方巾给他擦拭嘴角血渍,不阴不阳道,“他心里乐着呢!”
薛壑擡眸看她,“缘何这般说,很疼的。”
正好做戏给明烨看,且御史台後继有人了。
江瞻云没说出来,触在他唇畔的手顿了顿,猛戳了一下,惹得薛壑‘嘶’了声。
“我笨手笨脚的,桑桑来吧。”她把方巾丢给侍女,坐在一旁不说话。
薛壑看了她两眼,只当临近婚期,落英心中惶恐,遂道,“方才不是自己都讲得很明白吗,我提议右扶风继续由孙氏族人担任,自有向陛下投诚之意,短时间内他不会动你,甚至可能礼遇你。你放心,宫内还有薛氏的人,都会保护你……”
江瞻云坐在临窗的位置,没有看薛壑,只将一双泛红的眼睛避向窗外,轻轻点了点头。
*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诚如薛壑所言,明烨礼遇薛九娘。虽说天子立後自有现成的规制,只需循例即可。
但在规制以外尚有允许稍微改动的地方。
比如,大婚的礼服庙服,上衣青色的深浅,领袖边缘的花色;再比新後入朱雀门时重翟车的装饰,鼓乐的择选等。
江瞻云自无心这处,七月下旬送来向煦台,她稍稍挑选後,月底前便送回宫中。
如此八月九月很是空闲。
说是新妇待嫁,又是皇後之尊,然向煦台中一切如常,朝中亦是难得的平静。
这日已经是十月天,距离十月十六的婚期不到十日。江瞻云身子恢复大好,午後歇晌不着,也没惊动人,披衣过来书房看书,顺带推演入宫後的计划。
她寻来两本之前看过的记载青州民谣的书简,席地而坐,慢慢阅过。
忽听窗外不知何时过来侍弄花草的侍女们闲话。
“我记得以前咱们家的女郎待嫁,这临近婚期可是忙得不亦乐乎。郑七公子一趟趟地派人来,今日问婚服可要再缀颗明珠,明日问迎亲的骏马可要换成河曲马,过两日又道是得了一匹天马,问女郎是否又骑马又坐轿辇。女郎自己是定了婚服要换腰封,择了珠冠又要重选妆面……两家尊长被他二位折腾得够呛,怎道了这处,这样静悄悄的。”
“傻子,那是咱们女郎同郑七公子门当户对,情深意重。这厢虽说帝後同尊,但到底是天子,地位比皇後高。七月里能谴人来问九姑娘那些事宜,便已经是万分恩宠了。这会九姑娘自然闲着无事,哪会同咱们女郎那样……”
两侍女原比较的是薛壑的胞姐,江瞻云没仔细去听,然後头却不知不觉竖起了耳朵,想起许久前自己和薛壑备婚时的那点事,想起不久前薛壑在她病床畔的一席话。
前尘往事汹涌而来,青年的话语点点敲击在心头,她抵拳在唇口,咬住了手背皮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