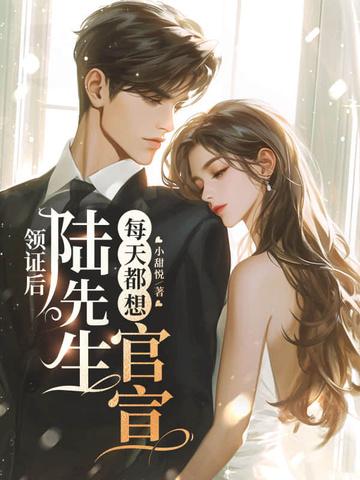富士小说>恋爱剧本高甜 > 第24章 番外 寂静之处(第1页)
第24章 番外 寂静之处(第1页)
(沈屹视角)
我的世界被一分为二。
不是以手术为界,而是以声音为限。左耳里的世界永远停留在了那个冬天,而右耳,成了我连接外界的唯一桥梁。
有时在深夜醒来,我会下意识地触摸左耳,仿佛那样就能唤醒那片沉睡的领域。白夜总是能立刻察觉我的动作,即使在睡梦中,他也会无意识地收紧环住我的手臂,像确认我的存在。
“还在适应?”今早他这样问我,手指轻轻梳理我的头。
我没有回答,只是靠向他。言语有时是多余的,特别是当他能读懂我每一个沉默的含义。
作为一名医生,我比任何人都清楚神经损伤的不可逆。理性上,我接受这个事实;但感性上,那个永远寂静的左耳,像生活中一个永恒的提醒——关于脆弱,关于失去,也关于接受。
直到我开始在研究中心工作,与那些带着各种“不完美”身体却依然追求卓越的人们共事,我才真正理解了李主任说过的话——局限不是终点,而是另一种。
今天下午,我主持了一场特殊的手术演示。患者是一位有轻微手部震颤的年轻医生,他因这个状况几乎放弃外科梦想。我们合作设计了一套稳定辅助系统,让他在保持精确度的同时,不必与自己的生理特点对抗。
手术成功后,他摘下口罩,眼中闪着泪光。
“沈医生,谢谢你没有告诉我‘你不适合做外科医生’。”
这句话在我心中回荡良久。曾几何时,我也害怕听到类似的判决。
回办公室的路上,我经过研究中心那条着名的“包容长廊”。墙上挂着团队成员的照片和简介,每一段文字都坦诚地讲述着各自的“不完美”——听力损失、视力障碍、行动不便、心理健康经历包括我和白夜的故事。
我的简介旁,白夜偷偷加了一行小字:“他教会我,爱是学会在寂静中倾听。”
我站在那行字前,久久不能移步。
“偷看自己的介绍?”白夜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笑意。
“你什么时候加的这句话?”
他走到我身边,与我一同注视着那面墙:“上周。合适吗?”
我握住他的手:“再合适不过。”
晚餐时,我们讨论了新项目的方向。白夜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开一套能让全聋患者“感受”音乐的系统。
“不是通过残余听力,而是通过触觉和视觉。”他的眼睛在餐厅柔和的灯光下闪闪光,“就像你教我的,当一种感官受限,其他感官会变得更加敏锐。”
我注视着他,这个曾经只关注自己痛苦的男人,如今却在为素未谋面的人寻找解决方案。成长,或许就是我们都能成为彼此更好的版本。
睡前,我在书房整理旧物,偶然翻到一本厚厚的笔记本。翻开一看,是我术后早期的康复记录——歪歪扭扭的字迹,记录着每一天的挫折和小小的进步。
有一页特别标注着:“今天独自走过整个走廊而没有失去平衡。白夜在尽头等我,笑得像个孩子。”
另一页写着:“他学会站在我的右侧说话,不再需要提醒。”
还有一页,只有简单一行:“他哭了,因为我说了一句‘我没事’。”
我从未意识到,自己记录了这么多细节。更未意识到,那些我认为微不足道的进步,在他眼中是何等珍贵的胜利。
“找到宝藏了?”白夜端着两杯热牛奶走进来。
我把笔记本递给他:“看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