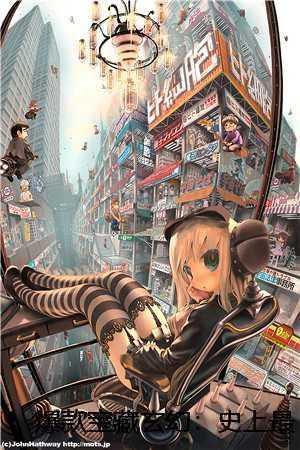富士小说>凤阙阶前守夜的黄豹 > 账房里的算盘(第1页)
账房里的算盘(第1页)
账房里的算盘
深秋的账房飘着墨香,凌酌月推开木门时,春桃正趴在账册上打盹,算盘珠散落得满桌都是。江南巡查回来後,她就忙着核民生坊各坊的账目,桌上堆着的账册比砖还厚,红笔批注的“盈利”“亏损”像串跳动的火苗。
“醒了?”凌酌月拿起件棉毯,轻轻搭在春桃肩上,“江南的账算完了?”
春桃猛地惊醒,揉着酸涩的眼睛:“公主!算完了!苏州织坊的姐妹自己办布庄,头个月就赚了五十两,除去成本,够给三十个织工发月钱了!”她翻出最底下的账册,上面贴着张红纸,是织工们按的红手印,“她们说要给您寄匹云锦,被我拦下了——我说公主不爱这些,不如多寄些江南的新织样,让咱们民生坊也学着织。”
凌酌月翻开账册,江南织工的字迹歪歪扭扭,却把“一尺布换多少米”“一匹绸赚多少银”写得清清楚楚。“做得好。”她指着账册上的“分红”栏,“让她们把盈利分三成给织工,剩下的存起来扩布庄,明年再多招些没活路的姐妹。”
账房外传来算盘声,是夜校的张婶带着姑娘们学算账。她们刚学了“复式记账法”,正用染坊的紫草账练习,噼啪的算珠声像在数着日子往前跑。
“张婶说,女医馆这个月义诊用了二十斤草药,得记在‘公益支出’里;农具坊卖了五十把锄头,盈利要分些给铁姑买铁料。”春桃指着墙上的总账,“咱们的账越来越细了,连谁领了多少米丶谁借了多少线,都记得明明白白。”
凌酌月望着墙上的总账,上面贴着各坊的收支条子:染坊的紫布换了三石米,女医馆的草药收了五两银,农校的新谷种结馀十斤……这些细碎的数字,比朝堂上的国库报表更让人心安,因为每一笔都连着女子的手,连着实实在在的日子。
“下个月起,”凌酌月拿起红笔,在总账旁添了行字,“各坊设‘女子互助银’,每月从盈利里提一成存着,谁家里有难处,就能借出来周转,不用再求别人。”
春桃眼睛一亮,立刻在账册上记下:“这个好!前几日织机房的阿翠娘病了,她想借银子抓药,又怕被人说‘女子家借钱不吉利’,硬挺着没说——有了互助银,她就不用熬着了。”
正说着,秦风掀帘进来,手里捧着份奏折。“公主,刑部递来的,说新律推行到蜀地,有个县丞不让女医开馆,还撕了医馆的牌子。”他的声音带着怒气,“按律该摘他的顶戴,可蜀地巡抚说‘女子行医本就破例,何必较真’,把案子压下来了。”
凌酌月接过奏折,红笔在“县丞撕牌”四个字上圈了圈,墨迹深得像要透纸而过。“让秦风带亲兵去蜀地。”她把奏折拍在桌上,算珠被震得噼啪作响,“告诉那个巡抚,新律不是摆设,女子的本事也不是‘破例’。撕医馆的牌子,就是打朝廷的脸,这顶戴必须摘。”
春桃攥着算盘的手紧了紧:“公主,我跟秦将军一起去!我带着江南织工的账册,让他们看看女子能赚多少银子,能救多少人命,再敢说‘破例’二字!”
凌酌月看着她眼里的光,那是从夜校的油灯里丶江南的织机旁丶账房的算珠间一点点攒起来的锐气。“好。”她把新律文书递给春桃,“你去告诉蜀地的女子,她们的医馆,朝廷护着;她们的本事,天下认着。”
暮色漫进账房时,春桃正对着算盘核“互助银”的账目,算珠声清脆得像碎冰。凌酌月望着窗外,民生坊的灯一盏盏亮起来,织机房的梭子声丶染坊的捶布声丶账房的算盘声混在一起,像支越来越响的歌。
她忽然想起母妃留在账册里的话:“女子的账,要算得比谁都清——算清自己的本事值多少,算清自己的日子该怎麽过,才算没白活一世。”
如今,春桃的算盘在算,张婶的账本在记,无数女子的手在数着自己挣来的铜板。这些数字堆起来,比太和殿的金砖更扎实,因为它们是给登基铺的路——不是急着迈上去,是让这条路的每块砖,都刻着“女子能行”的印记。
而凌酌月要做的,就是让这印记刻得再深些,让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再踏实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