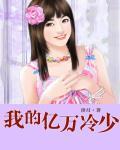富士小说>雪覆是什么意思 > 廷议决(第1页)
廷议决(第1页)
廷议决
昭熹元年的第一次大朝会,在太极殿举行。
新帝登基,万象更新,但摆在面前的,却是一个历经战火丶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北境虽定,但边防需重整;战火虽灭,但民生需恢复;朝堂虽立,但官员需考核,制度需厘定;更有那西市尚未干涸的血迹,所带来的隐忧与议论,仍需安抚与疏导。
封庭筠高坐于御座之上,冕旒垂面,神色肃穆。他目光扫过殿下济济一堂的文武百官,沉声道:“衆卿,今日廷议,事关国本,皆可畅所欲言。”
话音刚落,新任户部尚书,一位原户部侍郎,以精于算计着称的老臣,便出班奏道:“陛下,如今国库空虚,前朝挥霍无度,加之战事耗费巨大,去岁各地赋税因战乱多有减免或未能足额征收,眼下朝廷各项开支,如官员俸禄丶军费丶赈济丶工程等,皆捉襟见肘。臣恳请陛下,允准加征明年春税,并清查各地豪强隐匿田亩,以充实国库。”
此议一出,立刻引起了议论。战乱方息,百姓喘息未定,此时加税,无异于竭泽而渔。
新任工部尚书,一位曾因直谏被前朝贬黜丶如今被起用的官员,立刻反驳:“陛下,不可!百姓久经战乱,困苦不堪,此时正应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岂能再加征敛?臣以为,当务之急,是减免赋税,鼓励垦荒,兴修水利,以苏民困!”
“减免赋税?说得轻巧!”户部尚书提高了声音,“国库无钱,拿什麽支付百官俸禄?拿什麽供养数十万大军?拿什麽赈济灾民,兴修水利?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百姓乃国之根本!若逼得民不聊生,纵有金山银山,又能如何?”工部尚书毫不相让。
双方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文官队列中,支持者与反对者皆有,一时间殿内嘈杂起来。
封庭筠静静听着,并未立刻表态。他知道双方都有道理,国库空虚是事实,民生凋敝也是事实。这其中的平衡,需要他这位帝王来权衡。
这时,新任吏部尚书,文若谦,出班奏道:“陛下,二位大人所言皆有道理。然臣以为,加税与减税,皆非上策。”
他顿了顿,继续道:“首先应当清理前朝弊政。如清查被权贵侵占的官田丶盐铁专卖之利被中饱私囊丶各地关卡乱收费等,将这些本应属于国库的收入收回,便是一大笔进项。同时,鼓励商贸,降低市税,使货物流通,商税自然增加。至于节流,则应裁撤冗馀机构,削减不必要的宫廷开支,整饬军备,提高军费使用之效。”
文若谦的话条理清晰,切中要害,顿时让殿内安静了不少。
封庭筠微微颔首:“文爱卿所言,深合朕意。清查田亩丶整顿盐铁丶鼓励商贸丶裁撤冗费,此四事,便由户部丶工部丶吏部丶御史台会同办理,文爱卿总揽其责,拟出详细章程,尽快施行。”
“臣,领旨!”文若谦躬身应道。
户部尚书与工部尚书对视一眼,虽仍有担忧,但见皇帝已有决断,且文若谦的方案确实更为稳妥,便也齐声道:“臣等遵旨。”
财政之事刚告一段落,韩冲便出班奏道:“陛下,北境边防乃重中之重。如今战事虽息,但草原各部狼子野心,不可不防。臣请旨,重整北境防线,加固关隘,补充军械粮草,并轮调部分久战之师回内地休整,以保持战力。”
“准。”封庭筠毫不犹豫,“北境防务,由韩卿与雷豹将军全权负责,所需钱粮,由户部优先拨付。”
“谢陛下!”韩冲与位列武将班次的雷豹同时出列,声如洪钟。
接着,又有官员奏报江南水患後修复丶漕运疏通丶科举取士等事宜,封庭筠皆仔细听取,与重臣商议後,一一做出决断。他思维敏捷,决策果决,虽是新君,却并无青涩犹豫之态,令不少原本心存疑虑的旧臣暗暗折服。
然而,就在廷议接近尾声,气氛渐趋缓和之时,一位原御史台的老臣,素以耿直敢言着称,忽然出班,手持玉笏,高声道:“陛下,臣有本奏!”
“讲。”
老臣深吸一口气,朗声道:“陛下!前朝赵氏,固然罪孽深重,然其血脉,尤其是那些未曾参与朝政丶甚至尚在稚龄的宗室子弟,一并处决……此举,虽快意恩仇,然终究有伤天和,恐非仁君所为!如今朝野之间,已有微词,恐伤及陛下圣誉,亦不利于新朝凝聚人心!臣冒死进谏,望陛下日後施政,当以宽仁为本,慎用杀伐!”
此言一出,满殿皆静。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位老臣身上,又偷偷瞥向御座上的皇帝。西市血案的阴影,终究是无法轻易抹去。这位老臣,可以说是说出了许多人心底不敢言说的话。
封庭筠端坐不动,冕旒的珠帘遮蔽了他的眼神,让人看不清他此刻的神情。殿内静得落针可闻,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