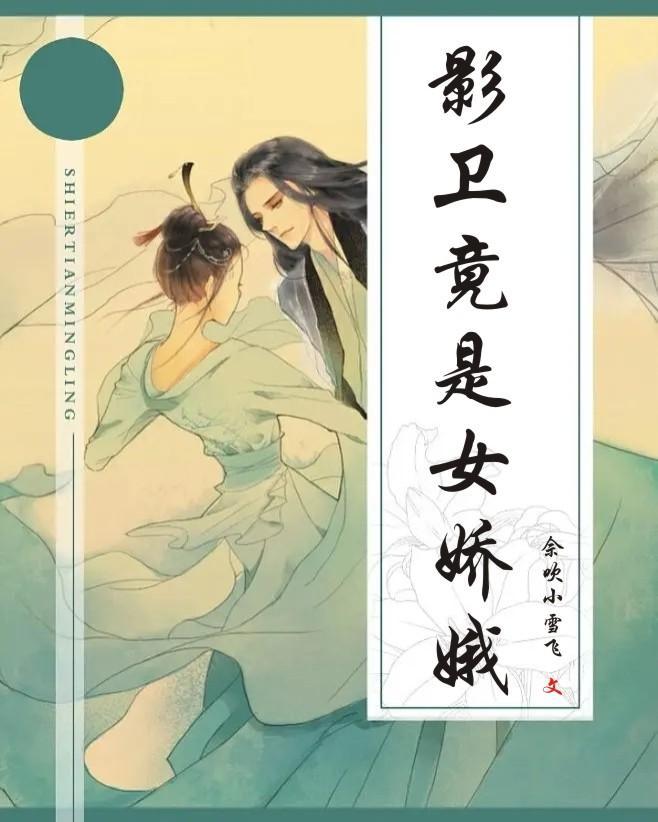富士小说>当我另嫁他时裴彧 > 第 50 章 不论从前还是往後我都(第4页)
第 50 章 不论从前还是往後我都(第4页)
“早知道,一开始我就不该让宋徽音进门。”
裴彧低笑起来,扯动背脊的伤心,他抽气道:“您若赶走了徽音,心心念念的孙子就没了。”
裴夫人翻了个白眼,一巴掌呼在裴彧血痕累累的背上,怒骂,“你就知道维护她,深怕你老娘找她麻烦是不是。”
裴彧捡起外衣披上,懒散的站在那里笑,“怕您找她麻烦,怕您给她气受,怕她伤心难受……”
“滚滚滚。”裴夫人装做要打人的样子赶人,“赶紧滚去上药。”
——
徽音视线在竹简上游离,距离裴彧和裴夫人离开已经过了半个时辰,她坐在这里也已经半个时辰,一个字都没有看进去。
她脑中满是裴彧玩世不恭的笑容,徽音撑着脑袋无奈的叹口气,良久,她把竹简摞好,起身出门。
手刚刚触碰到纱帘,就见裴彧一瘸一拐的走来,外衣松松垮垮的披在肩侧,里衣下摆沾满血迹。
徽音呼吸骤停,撩开纱帘小跑过去,手足无措的立在裴彧面前,“你……你怎麽了?”
裴彧面色痛苦的吸口气,站不稳的倒在徽音身上,“好疼啊。”
徽音虚虚扶住他,不小心碰他身上的伤,换来裴彧一阵闷哼。她顿时吓住不敢乱动,“你还好吗?”
裴彧难耐的喘了口气,“疼死了。”
徽音扶住他的肩膀带着他向前走,馀光里全是裴彧苍白的唇色和冷汗淋淋的额头,她突然感到一股不可明说的难受,徽音抿着唇,“傅母,打盆干净的水来。”
进了屋,裴彧身形重,徽音扶着他脚步踉跄的倒在榻上,她让裴彧趴好,脱掉他的外衣,底下素白的里衣满是血色。
她呼出一口气,轻轻揭开裴彧的里衣,露出里面血痕交错的杖伤,徽音胸口闷闷的难受,连声音都低了两分,“你到底是做什麽了,惹得夫人如此生气,竟还动手了。”
裴彧侧着脸,瞅着徽音担心的面容,心中一阵舒爽。他沧桑的叹口气,摇着头不语。
徽音等了片刻,没忍住又问道:“你说呀。”
裴彧单手支着头,用手勾了勾徽音,指着身边的位置示意徽音坐下。
许了受了伤,他的声音有些暗哑:“阿母同我说李莹月的母亲是这几年来唯一真心愿意和她交好之人,也不曾私下嘲笑过她的出身。她有心和李家交好,叫我今日陪她去李家做客。”
裴彧顿了顿,偷偷摸摸的牵住徽音的手,见她没拒绝,更加放肆的十指紧扣住,“从前确实经常有人嘲笑我阿母出身小门小户,她这些年里也没几个知心好友,我没想太多便应了下来,後来才得知她有意和李家结亲。”
徽音睫毛轻颤,“然後呢?”
“今晨我告诉她让她先行去李府做客,实则是找到李大人告诉他我没有要和李家结亲的意思,全是阿母一人的意愿。”
“然後我便回了迎风馆。”
徽音点点头,唇角轻漾,“回迎风馆将我这里的竈屋险些拆了,颜娘拉着我抱怨了半天。”
“你笑了。”裴彧猛然翻身坐起,动作牵连身後的伤口,他只皱皱眉,看着徽音问,“你这下是真的不生气了?”
徽音收了笑意,抿着看着他,“你先躺好。”
裴彧乖乖躺下去。
颜娘将清水和干净帕子放在榻边,将裴夫人刚刚吩咐人送过来的伤药也留下,轻手轻脚的退出去。
徽音拧干帕子,小心翼翼的擦拭裴彧背上的血痕,伤口横亘颇深,处罚之人手劲颇大,没半个月消不下去。
裴彧感受着後背徽音柔软都手掌在他背上轻抚,身体控制不住的颤栗,就像一片轻柔羽毛在背後来回扫动,疼痛和舒爽感遍布全身,爽得他眯起眼角轻轻呼气。
徽音看着身下人颤抖的背脊,以为是弄疼了他,动作不由得放更轻,这番小心翼翼的擦完他身上的血迹,徽音也累出一身汗。
她取过伤药均匀的倒在裴彧的背脊,苦涩的药味扑面而来,徽音用手轻轻抹开。
“嘶。”
裴彧突然弓起身,徽音的指甲不由得戳到他的伤口。
“怎麽了?”徽音放下药,凑近裴彧跟前问。
裴彧的耳尖通红,他弓着的身体慢慢放回去,方才徽音摸到他的肩胛骨,他那独守空房的小兄弟受不了这个刺激,当即反应起来。
这麽丢脸的事情当然不能说出口,裴彧头埋进软枕里,闷闷道:“没事。”
徽音看着他通红的後颈,伸手去探他的额头。
裴彧跟受惊的猫一样,条件反射的往後退。
徽音的手蹲在原地,看着他不自然的身体姿态,疑问,“你到底怎麽了,哪不舒服?”
裴彧望着她清澈的眼底,终是忍不住心中的蠢蠢欲动,将人拉进怀里轻吻。